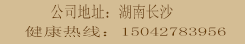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习性 > 叙拉古之惑千古莫须有文彦博的坑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习性 > 叙拉古之惑千古莫须有文彦博的坑

![]()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习性 > 叙拉古之惑千古莫须有文彦博的坑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习性 > 叙拉古之惑千古莫须有文彦博的坑
叙拉古之惑案:最近刚完成了一篇论文,因为还没有发表,故不多言。完成一篇论文,肯定是需要阅读大量的研究,最终完成论文后,有些材料也没有用进去,这不免有点可惜,所以,我就酝酿再写一篇大文章,题目就叫《秦相当国》,这篇文章的具体思路保密,因为还要阅读很多材料,一个月内估计也出不来。不过,这里倒是可以根据我现在掌握的两份材料,做一点讨论,得出一个开脑洞的结论,主要目的是让读者在理解历史的时候,不要简单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与其说这篇文章是说个故事,不如说是教大家一点独立思考的方法,毕竟不是“芝麻开门”一样,标榜一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史答案就会自动呈现在人面前。
一
历史这东西,因为不是什么谋生技能,所以,我们往往拿来做一种文化的消遣,不是太重视,二来,也不是各个人(包括很多历史从业者)有天赋去理解历史(至于我嘛,当然是天赋异禀啦,哈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理解历史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陷入一种脸谱化的理解,在一种二元的叙事视野下,好人做什么事,总能够得到我们的同情,坏人做了什么事,总会反面强化我们的厌恶情绪。秦桧秦相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脸谱化历史人物。真实的秦桧要复杂的多,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由待后文翻案。
二
说起秦桧,我们总会条件反射式的把“莫须有”这三个字和他联系起来,南宋政权处死岳飞,大将韩世忠气愤不过,前去质问秦桧,最权威的史料记载当然是《宋史·岳飞传》: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大致介绍一下这段对话的背景,就是说岳飞儿子岳云和岳飞账下头号大将张宪有一封书信,岳云指使张宪谎报军情,试图让岳飞官复原职,这份信是伪造的,反正南宋朝廷就借口把岳飞下狱了。大将韩世忠为岳飞鸣冤,就跑去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虽然岳云和张宪的书信确实有疑问,但这事情不需要有理由(稍微会具体解释,为什么这里要被翻译成“不需要有”),韩世忠说这“不需要有”怎么能说服人心呐?
关于这段事情,宋代至少有十多部史籍都做了记载,从内容上来看,大同小异,显然是同出一个史源。后世对其进行引用,一般是元人编撰的《宋史》和岳飞之孙岳珂编著的《鄂国金陀粹编》两书,一部是正史,一部是有关于岳飞最详细最源头性的史料集,都比较常见,所以引用比较多。《宋史》成书比较晚,关于岳飞的记载,大部分沿袭《鄂国金陀粹编》的说法,也就是说,正史中的岳飞形象很大程度也是来自岳飞孙子的说法。如果我们不以太多情感代入去看待这里的史源问题,一定是会保持警惕的,毕竟是孙子给爷爷翻案所编写的书。这叙事的可靠性,不需要什么史学训练,也可以意识到肯定有很多情感因素在里面。我作过一个比方:今人拿岳飞的孙子编写的史书把岳飞当做军神,其白痴程度不啻于一千年后的人拿当代著名孙子给爷爷立的传记当信史,这里我们不做价值判断,但至少有一点肯定大家没有疑意,他真实的爷爷肯定比他笔下的形象要复杂的多(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除了岳珂的史料之外的史料记载,并不足以建构一个完整的岳飞形象,故而历史学家也不得不采其说。有时候,历史学家也是要面对明知不可信而取之的无奈)。
其实岳珂这部《鄂国金陀粹编》也是历来就受到质疑,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就认为其中有不少附会之辞,不足具信。据宋史学家顾吉辰的考证,“莫须有”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来自于宋人熊克的《中兴小记》,此人出生年月最早,几乎和岳飞、秦桧、韩世忠是同代人,现有关于韩世忠和秦桧对话的出处最早的出处就是来自于此。但是熊克在记载这段对话的时候,注了一句:“此据《野史》”。也就是说,这句话真正的出处并不可靠,连一个署名都没有,虽然我们不能贸然的认为这种野史就一定记载不真实,但是我们看到关于南宋历史最重要的两位历史学家无论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还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没有采纳这一说法,这说明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是令人怀疑的。
其实,根据我们平时谈政治的经验来说,时常会遇到一些毫无根据的编造,通常我们也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不予采信。即使有些有明确说法的史源,历史学家也会根据洞察力不予采信,比如说,李敖根据一部回忆录,披露宋美龄和美国政要威尔基上床的说法,杨天石老师就专文做了反驳。之所以后世的史书作者会采信这种说法,多半是一种心理迎合,这里又涉及到具体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历史人物的形象制作问题,典型如49年10月1日,毛泽东并没有说过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话,只说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如果没有影像资料的铁证,我们还真不用怀疑,几百年后的人会直接把这句附会的话当做信史。如果要展开说明意识形态和人物形象制作的问题,又是一番长篇大论,此处就不展开的。总之,这句话的真实可信度,不会高于香港街头那些政治八卦刊物(包括指控秦桧是金人奸细的说法,均是时人诼谣)。
三
文章写到这里,我等于是把顾吉辰的观点介绍了一下(当然我们是不谋而合,只不过他找了很多材料),如果是这样,显然我没资格吹嘘自己,这就要引申出标题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文彦博。
文彦博“介休三贤”之一,北宋名相,后人对其评价,几乎是一边倒点赞,摘录一些评价,可以窥见一斑:
苏轼: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
苏辙:惟判府司徒侍中,辅相三世,始终一心。器业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无为而庶务以成。
脱脱: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建是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丰而降,弼、彦博相继衰老,憸人无忌,善类沦胥,而宋业衰矣!《书》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岂不信然哉!
敖英:文潞公处大事以严,韩魏公处大事以胆,范文正公处大事曲尽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
孙承恩:休休元臣,堂堂大耄。端雅静重,镇压浮躁。危疑定策,社稷之功。天下异人,夷使改容。[47]
李廷机:良臣文彦博,贤宰欧阳修。公心同协政,奸党绝交游。
皆是溢美之词吧?(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见到“儒家宪政”老是喜欢引用文彦博那句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其实后面还有半句“非与百姓治天下”)但是他偏偏说过一句类似于“莫须有”的话,迫害过一个有宋一朝仅次于岳飞的名将狄青。
狄青因为战功官升至枢密使,要知道岳飞后来也只有做到枢密副使。这在重文轻武的宋朝,不免引来很多文官的不快,当时有舆论借口彗星,要把外放青州。文彦博当时是宰相,力主此议。据王大成的《野老纪闻》的记载:
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时文潞公(彦博)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遭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日:“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自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庶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阿,青阁中使来,抑惊疑终日,不半车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
就是说,当朝宰相文彦博找了个借口,说狄青骄横跋扈,所以要外放他,然后狄青跑去和宋仁宗说,我又没什么过失,把我外放,这说不过去吧。宋仁宗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然后就找文彦博来商量,宋仁宗说了一句:不管怎么样,狄青是忠臣,然后文彦博就怼了回去:太祖当年难道不是周世宗柴荣的忠臣吗?但是形势所迫,所以才接受了黄袍加身。祭出这样“政治正确”的大旗,宋仁宗也没有话说了。然后狄青跑去向文彦博要个说法,文彦博朝他望了一眼,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没什么原因,朝廷(我)不相信你。狄青出京之后,文彦博还经常派人来看他,其实就是监视,找茬,最终不到半年,狄青就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下被吓死了。
我开篇就说过,二元脸谱的理解往往会主导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我们会天然的同情他们所处的立场,比如说文彦博这种行为,后世理解起来,往往会从宋朝“祖宗之法”的角度,为他开脱。再者,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逻辑去理解秦桧,就会面对“情绪结构”(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我觉得历史叙事就是各种情感结构的合力作用,当然目前我并没有想的很仔细,就不展开了)的困境,同样一件事,同样一段蛮不讲理的对话,我们就不能以“祖宗之法”来为秦桧开脱,在这种“情绪结构”下,大部分人断然拒绝这种合理的解释。
四
虽然,我个人倾向于秦桧和韩世忠的对话是虚构的,但是我这里要处理一个问题,所以先说说“莫须有”这个词为什么白话文要翻译为“不需要”。
过往对于这个词的翻译存在很多争议,一般来说,有着几种解释,解释一:或许有;解释二:必须有;解释三:难道没有?
我们对照原话“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来套一下:
1.岳云和张宪这封书信虽然存疑,但是事情或许有。
这句话里存在语境转折明显不连贯,底气不足。
2.岳云和张宪这封书信虽然存疑,但是事情肯定有。
这句话,虽然在语境转折上可以成立,但是作为一件要昭告天下的案子,这样说,就难以服众了。但秦桧作为一个政治家,以他的政治智慧,说话肯定不会那么幼稚。
3.岳云和张宪这封书信虽然存疑,但是难道没有其他谋逆的事情吗。
这句话在语境上也成立,但是我们要注意具体语境,韩世忠随即反诘了一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个语境很关键,秦桧表达的意思如果是,虽然书信可能是假的,但是还有其他事情。那么韩世忠顺着这个回答的反应应该是反问,还有什么事?而不是反诘,“难道没有其他事”这么能让天下人服气?
以上三种解释都存在语境不通顺或者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应该存在第四种解释,就是“不需要什么理由”
岳珂在编写《鄂王金陀粹编》的时候是有意回避宋高宗的态度的,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怕触犯皇权。但事实上,宋高宗的态度是坚决的,所以秦桧把岳飞做掉,是有恃无恐的,因此他在回答韩世忠的时候,是相当傲慢并且有底气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回答应该是:岳云和张宪这封书信虽然存疑,但是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然后韩世忠才会反问,不需要理由这怎么能让天下人服气啊?
再此,我们还可以找一些宋人的文字进行一下训诂比较。《宝真斋法书赞》有“莫须与他明辩”之语,《曲淆旧闻》有“莫须待介甫参告否”之语,《铁围山丛谈》有“莫须问他否”之语,《思陵录》有“莫须批出”之语,《後村大全集》有“莫须有人”之语,又如《分类夷坚志》有“莫须谢尚书否”之语。
这些用法都可以用“不需要”来解释。
五
之所以不厌其烦的解释一个我认为完全是编造的对话,其实是要想说明,秦桧这段对话其实是拷贝自文彦博那句:“无他,朝廷疑尔。”
我当时读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惊讶,同是两个权相,同是迫害两个盖代名将,而权相对此的回应的口气和态度,居然是一模一样。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我当即就怀疑“莫须有”这三个字多半是从前者拷贝来的。后来一查,果然,“莫须有”并没有可靠的出处,而是来自民间的说法。那么历史的真实完全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文彦博说了“无他,朝廷疑尔”这句话,被人记载下来,一直有流传,到了南宋时期,因为相同的处境,有人很容易去开展联想,将前者的话做了一点改变,附会到秦桧身上去。这不是一种真实的记载,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象制作(这里,完全不用考虑,秦桧说过这句话,以秦桧的精明,既然要办岳飞,怎么可能找不出借口呢,随便找个诬告的证词,就可以把韩世忠顶回去,完全没必要说“不需要理由”,以落人口实。秦桧这样一个干练的宰相,连个借口都找不出来,这说出来,有人信?)。
肯定有人会质疑我这样的想法,过于自我补脑。嘿嘿,我还偏偏找到一点现实案例。袁腾飞在“百家讲坛”上讲《两宋风云》的时候,他就移花接木的补脑了一个场景,而这个场景正好是拿文彦博的段子嫁接到秦桧身上的。
哎哟喂,这里的嫁接,不正是宋仁宗和文彦博这句话吗:“(仁宗)且言狄青忠臣。公日: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事实上我核查了一下古籍库,发现宋高宗和秦桧根本没有类似的对话,也就是说,这句话唯一的出处是就是宋仁宗和文彦博。
我们这里不用去计较袁腾飞的嫁接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哪一点,确实会存在一种历史拷贝的问题。哪怕是今天历史学的方法已经很严谨了,还是出现了这种状况,这里其实涉及到一种大众心理无意识的形象制作和接受问题。
六
政治史的记载,通常是带有很强的价值目的的,所以这类记载的信息多少存在这偏差,这不同于其他统计数据或者社会史的史料。所以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在面对政治史的史料时,必须以一种警察审问犯人的态度,对犯人的每一句话都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并且做出严厉的讯问。这里重温一下我精神导师说的那句话: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要见了风就是雨,接到这些信息,你们本身也要做判断,假使这些无中生有的东西,你再帮他说一遍,将来在宣传上出了偏差,你们也有责任的。
今天我在散步时,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人惯于接受的一个黑白二元对立形象,倒不一定是一个智力问题。我说过,大部分人并没有兴趣去理解历史,通常而言,历史对于人来说,不过就是一个故事,无所谓真假。但是对于历史学家,那就不能以普通人的要求对待了。
之所以造成今天,秦桧被污名化,除了历史和特定的政治背景之外。在今天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之下,我们的历史学家也负有不小的责任。我们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过去一个时期内的历史学家,完全缺乏相应的学科自省能力(现在的历史学家基本上不再有上一代人那种时代烙印了)。他们的历史叙事,刻意强调黑白的二元对立,完全是迎合一种简单的审美旨趣。
说他们是历史学家吧,他们又不具备历史学家所应该具备的历史复杂情境的能力。说他们是美学家吧,他们又根本不具备相关的理论自觉意识。虽然他们日常和史料打交道,但是其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按照一个美学理型,拿史料来完成一件美学作品,说穿了,不过就是一个美学家的美学建筑包工头。真要说他们是历史学家,那就等于说一个矿工是个地质学家。
今天,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在面对岳飞、秦桧、赵构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要敢于打破旧有的美学形象,挑战这些史学矿工的话语霸权。
在信息爆炸,学术脱变的时代,本白癜风早期症状白殿疯不治会怎么样
转载请注明:http://www.haikuoyua.com/ymdc/13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