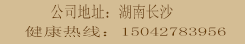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种类 > 要是能重来,我不再独裁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种类 > 要是能重来,我不再独裁

![]()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种类 > 要是能重来,我不再独裁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种类 > 要是能重来,我不再独裁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
....
....
....
那特么也是虚构!!
ChapterI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
10天前我度过了56岁生日。
也许是很久没有到地上活动吧,
那天的天气好极了,
宴会厅格外敞亮。
宴会上,
希姆莱、戈林、葛培尔
在谈论着帝国重归荣光的愿景,
因为前一周的好消息,
罗斯福老小子脑溢血一命呜呼。
本以为战争会就此出现转折,
没想到这帮背叛、懦弱的人对溃败知情不报。
如今败局已定,
戈林这二傻子还妄想取代我成为新的元首,
而希姆莱
竟以出卖我作为与盟军和谈的条件。
这俩青沟子娃娃真是
tooyoung,toosimple。
我太知道斯大林和丘吉尔了,
但愿这俩叛徒被他们送去奥斯维辛,
被齐克隆B熏成腊肉。
只有葛培尔是我最忠诚的伙伴,
我请他做我和爱娃的证婚人。
就在昨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在和我一起结束生命之前,
我得给她个名分。
这几天我的帕金森加重了,
晚上总是睡不好,
时常梦见往日那段青葱的岁月......
大家好我叫阿道夫·希特勒
一个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男子
据说这种开场白的正确打开方式
是捏着鼻子发出两倍的语速。
年4月20日,
我出生在奥地利小镇“不劳脑”,
按理说我日后应该是个善良单纯的人。
说起我的祖国奥地利,
我为它和奥地利人民感到自豪。
因为他们成功地让后人误以为,
我是德国人,贝多芬是奥地利人。
关于我的身世,
我觉得是世界上最难的问题之一,
真佩服远在东方的那些中国人,
他们怎么能分得清三姑六婆七舅八姨父什么的。
在我看来他们那只有年轻人和长辈的区别,
因为每年那项固定的仪式——
冬天里总有
那么几天长辈们都问年轻人同样的话题,例如
每月挣多少钱啊,
什么时候结婚啊,
什么时候要一胎二胎三胎四胎......
我天资聪敏在“不劳脑”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仅用2年光景便背下了那首高难度儿歌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说起我爷爷,
有人说我奶奶曾经在附近的犹太财主家当过佣人,
后来便有了我爸。
这话估计是琼瑶阿姨或张恨水叔叔说的,
不过我爸的人生
的确像极了鸳鸯蝴蝶派剧情。
我们老希家还是有勤奋的基因,
尽管我爸是私生子,
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了个海关小吏,
也算得出人头地。
48岁那年老希头娶了比自己小23岁的侄女
(或是外甥女,反正都管我爸叫uncle),
也就是我妈。
以至于我从小管我妈叫阿姨,
管我爸叫糟老头子
(虽然当时只敢在心里面这么叫)。
糟老头子坏得很,
经常揍我,尤其是喝大酒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谢他当年读了点书,
给我起了阿道夫这样的名字,
凭借ADF的首字母,
我在好友通讯录里能排在头几名。
早知道后来应去做微商的...
相比之下我的小日本老铁就没我这么好,
他老爹没文化,56岁才生了他,
于是给他取名高野五十六。
估计他对他老爹怀恨在心,
所以后来改姓了山本。
他们家就没有勤奋的基因,
这小子成天除了赌博撩妹啥也不会。
说起他我就来气,
说好一起夹攻苏联,
让他猥琐发育,别浪。
这小子在海上脑子进了水,
以为珍珠港里真有珍珠,还跑去偷袭人家,
结果把美国拉进了盟军阵营,
自己还赔了小命,
害老子最后没吃到鸡,
真是猪一样的队友。
再说回我爸,或者我大姨夫,
反正都是他。
因为他和我阿姨的结合,
我过年少走好几家亲戚,省不少钱。
糟老头子动辄对我拳打脚踢,
还人格攻击,
我幼小的心灵
几乎每天都受到上万点暴击,
唯一的好处就是打厚了我的脸皮。
我阿姨(也就是我妈)为了弥补我心灵的创伤,
对我百般呵护和溺爱。
所以我的童年就是
每天遭受家暴和宠溺的极端待遇,
这造就了我日后炸毛的性格。
这种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
我只有靠听相声来排解忧愁,
也就是这段时间,
我学会了好多贯口。
哪个是《报菜名》、
什么叫《八扇屏》、
《地理图》,
我全都倒背如流。
和糟老头子顶嘴,
我最爱学捧哏的那句“去你的吧”,
这段经历练就了我日后演讲的好口才。
ChapterII
到我14岁那年,
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糟老头子有天喝大酒,
从此再也不会打我了。
我和阿姨相依为命,
她希望我和糟老头子一样,
成为一名公务人员,
这显然不是文青的追求。
那会儿还没有互联网,
相声还不流行。
我创办的“特乐社”没干几天就关门了。
我这一身的艺术细菌眼看就要荒废,
直到有一天,
那些油布上的颜料,
为这个小镇青年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窗口。
大约一个世纪前,
从东洋运来的瓷器上用了非常特别的包装纸,
从它们被巴黎的艺术家们发现,
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竟然可以不用透视法,
通过平面也能完美地展示空间的壮阔。
几经打听,人们才知道,
那种画叫浮世绘。
现实版的买椟还珠发生了,
每到港一批瓷器,
印着浮世绘的包装纸都被一抢而光。
从那以后,
美术圈刮起了新一轮创新的春风,
各种风格的作品从巴黎蔓延到全欧洲。
长大后当画家
几乎是我们80后这代多数人的理想,
就像一百年后,
某国有批80后孩子
从小的理想是成为科学家一样。
相声这条路走不通,
我开始往画家转型。
我最喜欢的是画建筑,
最讨厌和一帮大老爷们围在一起,
画那些伤风败俗的大胖娘们儿。
为了新的理想,
我决定去首都维也纳求学,
那里全是金碧辉煌的巴洛克式建筑,
而我的理想是考入维也纳艺术学院。
好景不长,
我在维也纳求学的第四年,
阿姨生病了。
医生说她身上长了叫“肿瘤”的东西,
将不久于人世。
作为她唯一的儿子,
我不得不放弃画画,
回到家里照顾她。
每当她吃到我做的饭,
我从未见过谁的胃口有那么好。
为了对抗寒冷,
我把厨房收拾得宽敞干净,
那里一年四季有暖炉,
我让阿姨睡在厨房里,
我自己也搁了一张小床陪她。
在我的细心照料下,
阿姨的病情拖了将近一年,
在圣诞树彩灯光芒的照耀下,
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而我面色苍白坐在一旁,
亲手为她画下了遗像,
作为永久的纪念。
她走以后,这辈子我再没吃过肉...
ChapterIII
19岁,
我成为了孤儿。
圣诞节后,
告别了母亲和家乡,
我重返“维漂”之路。
5年来,
凭借对绘画的热爱,
即使在人才云集的维也纳,
我的建筑画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但我最终还是被艺术学院拒之门外,
原因是我不会画人体,
尤其是裸体。
每当我对着那些裸模,
羞涩的心情会让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发抖,
这时我都把头偏向一边,
但又总是忍不住偷瞄几眼。
那个年代的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
而维也纳是艺术的中心。
繁华的都市总是不乏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
作为奥匈帝国的首都,
这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学者、
左派革命和文青。
维也纳的繁荣,
让住在美景宫里的太子费迪南迫不及待地想继位。
作为他的子民,
我几乎没有受过他的任何恩惠。
谁知三年后他的死,
却几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此之前,
除了画画,
闲时我会去泡街上的咖啡馆。
那时候,
咖啡馆是学者和左派激进分子
经常讨论和演讲的场所。
在环城大道上的朗特慢咖啡,
有个叫弗洛伊德的犹太佬特别受欢迎,
贵妇们总是抢着把手递给他,
让他给摸骨算命什么的。
他是维也纳著名的“妇女之宝”。
这厮的工作室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听说他会解梦,
找他聊个天居然要提前1个多月预约,
我1月的伙食费不够跟他聊1小时。
维也纳的犹太人没有穷鬼,
他们肯定使用了骗钱的巫术,
随便做点什么就能忽悠到很多钱。
我估计,
他们要从那会儿开始卖大力丸,
现在一定是直销行业的寡头。
这些犹太富商的存在,
加上生活的失意,
让我逐渐从文青变成了愤青。
当时谁要给我一套女学生制服,
我一定代表月亮消灭他们!
中央咖啡馆我去得最多,
从我住处走路不到5分钟。
那里是革命热血屌丝的集散地,
大家讨论的全都是些反动激进的话题。
每当我想发泄心头的愤恨,
我就去那跟他们一起打鸡血,
顺便学学他们耍嘴皮子的功夫。
每次去的时候都能碰到几张熟悉的面孔,
他们是那里的常客。
其中有个格鲁吉亚大胡子叫
“啪啪的什么螺丝”,
名字太长谁都记不住。
这哥们日耳曼语都说不利索,
还贼特么爱嘚吧,
跟人说话的时候通常要重复好几遍,
大家都管他叫科巴(磕巴)。
有天上午,
科巴和一个叫托洛茨基的老毛子在准备同乡会。
我正从旁边经过,
不经意间和他对视了一眼。
那一瞬间,
从他瞳孔的深处突然跑出一群猛兽冲我咆哮,
而我的小宇宙瞬间爆发出一片闪电雷鸣。
这虽然听起来很荒唐,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会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那次之后,
科巴再没来过咖啡馆,
后来有人在圣彼得堡见过他,
当时他正领着一帮工人闹事,
旁边的人都叫他——
“斯大林同志”。
ChapterIV
苦逼的日子总是很漫长,
我没能进入艺术学院,
光靠卖画无法维持生计。
维漂的几年我不停地换工作,
帮人掸地毯、扫雪,
在车站推箱子,吃着没有营养的食物...
生活的落魄
已经让我变成了愤世嫉俗的魔鬼,
又过了一年,
就在我最揭不开锅的时候,
国内却炸开了锅。
太子费迪南被一个塞尔维亚愤青枪杀了,
国王发布了讨贼檄文。
谁知这仗一开打,最终引起的,
是整个欧洲皇室之间的战争,
后来这场战争被称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为新时代的爱国青年,
我也加入了报名参军的队伍,
奈何当时饿得营养不良,
体检没过被刷了下来。
听说南边的巴伐利亚打仗缺兵,
是个带把儿的就收。
为了有口饭吃,
我果断南下加入了德军。
我把内心的愤恨一股脑都发泄在了战场上,
凭借我英勇的表现,
仅半年就从一个传令兵升到了下士。
在一次战役中,
作为幸存者之一,
我被破格授予了铁十字勋章,
这种勋章通常不发给士兵。
我这人命大,
有个事情就能说明。
一天我正和战友们吃午餐,
突然听见有个声音叫我走开点,
于是我走过去看看是谁在说话。
还没走多远,
就在我刚才站的地方落下了一枚流弹,
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飞了。
不是哥吹,
直到战争结束,
哥就负过一次伤。
那次敌人使用了毒气,
逃过一死的士兵全都被熏瞎了眼睛.
多亏哥以前在画室偷看裸体模特儿时
练就的火眼金睛,
得救之后我只是暂时的失明。
令人心灰意冷的是,
当我的眼睛拆除纱布后,
战争已经结束了。
ChapterV
战后德军只允许保留10万人,
我光顾着打仗没办落户,
只能被裁。
好在当时人心不稳,
慕尼黑情报部门需要大量调查人员,
于是我成了名侦探希特勒。
有次被派去监视德国工人党,
他们在一家啤酒馆聚会,
台上讲话那哥们感觉嘴里是有袜子,
说了不到半小时,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鼾声,
我站在门口都快睡着了。
我一看今天肯定是打酱油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上台给背了段《报菜名》: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
烧花鸭,烧雏鸡儿,烧子鹅...
到底是童子功,
这一下台下一帮老爷们儿全都惊醒了,
南方人没听过相声啊。
一段不尽兴,
我又给大伙儿说了段单口《白蛇传》。
最后观众实在不让走,
我又返场唱了段小曲儿
《送情郎》和《探清水河》。
这一表演不得了,
工党的秘书把我看上了,
死皮赖脸非要我加入。
最后我没办法,
只好同意。
接过党员证一看,
我勒个去,
我是第97名党员,
这收个党费还不够吃个烤猪肘子的。
这时体现我艺术才华的机会来了,
在我的策划下,
我们准备把这个小党重新包装上市。
首先我们改了个响亮名字,
叫“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后来大家反映名字太长念不下来。
经大会讨论决定,
取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德语首字母
“N-A-Z-I”代替,
读作“纳粹”。
名字定了还得有个logo,
日耳曼人的祖先是古雅利安人,
我曾在古书上看到过“卐”字符,
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使命”,
再配上深红的背景,
这样一眼就能叫人印象深刻。
我还设计了纳粹党专属的制服,
采取“制服诱惑”吸引更多得了白癜风可以治好吗北京哪里看白癜风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haikuoyua.com/ymjj/36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