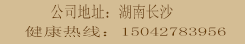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生活环境 > 续6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生活环境 > 续6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

![]()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生活环境 > 续6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生活环境 > 续6你是我不能说的秘密
提示:点击↑上方欲春楼我!
接上集继续开始阅读:
他扯着我的胳膊把我拖进卧室,胳膊像要被捏碎了般,一把把我甩到床上,看我的眼神有些绝望的意味。我挣扎着起来,又被他一把推倒,粗暴地扯了我衣服,强行掠夺。我痛得大叫,他不管不顾地横冲直撞,我抬起泪眼倔强地看着他,他一把捂上我的眼睛。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对我这么粗暴,但我的心情却有了变化。从最初的恨,恨不得杀了他,到后来的无奈、强忍,再到后来的无助、接受;到后来的心甘情愿,如今的他,再让我疼痛,我却已经没法恨起他来。只是说不上来地苍凉,说不上地挣扎。在快乐与痛楚间纠结着,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我不是没有心,这么多日子来,他的心思我不是不知道,可是他又是那么残忍,这种残忍会不会早晚落到我头上?到时我又该如何自处?
那是我第一次心那么痛,尤其是当自己随他如冰峰烈焰般燃烧的时候,那种痛尤其尖刻地撕裂着我的心,那一瞬间,我真的就想死在他的怀里,就那么死了算了,不用纠结任何问题,该不该的问题,会不会的问题……统统不用去想。我哭着低声喊:“你为什么不弄死我,我就不用这么痛苦。”
他的声音喘息着:“你还会痛苦?你没心。”纠缠中我哭着了,他抱着我微微颤抖,声音有些沙哑:“小薇,你如果说直到现在,你心里还是没有我,我立即放你走。”咬咬牙又补了一句,“这辈子都不再纠缠你。”我无力地抬眼看他,他的眸子里像什么碎裂了般的痛楚,我拼尽了全身的力气般,咬着牙说:“直到现在,我……”我的声音开始抖,进而全身剧烈地抖,我想说,可是我的心疼得说不出来,那种疼,像用冰刀在剜一样,除了疼,还有冷。
他一把把我紧紧的抱住,沉声说:“别说了,我不逼你。”自嘲地冷笑了两声:“这是我的报应。”说完狂乱地吻我的眼,我的唇,吻得我喘不上气,吻了很久,他松开手,摸摸我的头发,说:“你不用走,就住在这儿也行,想搬走也行,你卡上有钱。我走。”说完很快地穿好衣服走了出去。让我惊呆的不是他今天的动作,是他最后这句话。在北京待了很久,我的心一直在一种仓皇中度过。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背,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住的地方,好的嫌贵,便宜的又出种种状况,在子清家的时候,一次次被人锁在门外的感觉,让我对房子这两个字特别的敏感。特别害怕搬家。可是他在最后,仍然没有赶我走。还没回过神,听着门哐当一声,我的心痛得像窒息似的,跳下床追到门口,已经听不到他的脚步声,我无力地滑坐在门口,哭着低声喊他的名字:“子越,子越,你别走啊。”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地上爬起来,拉着箱子打车去了艾云家,进屋就是倒头大哭,直哭得全身抽空,没有力气。看我这样子,艾云反倒有些害怕,止住了自己的哭,喂了我几口红酒定了定神。我抽抽搭搭地和她说了我和冯子越的事情,艾云的嘴半天没合上,大口灌了几杯酒后骂:“真他妈见识了,你和那老狐狸演苦情戏呢?”艾云使劲晃着我:“小薇,你玩不过他的。”叹口气说:“之前我知道你躲着一个人,那时候林育诚天天不回家,回来也不和我说话,玩冷暴力,我还劝你,只要有人爱你,你就跟了,管它什么名分的,有人爱有钱拿,比我这守活寡强多了。后来幼珍被甩了,我辗转听人说是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跟了冯子越。当时就替你捏把汗,冯子越上过的女人比咱们见过的都多,在圈里是有名的花,还有好几个包长期的,偏偏那时候正是林育诚妈来了先逼我离婚,和他妈吵了半个月,乱七八糟的事没顾上找你。上次想找你你又有事儿,听你说幼珍的孩子,我一打听,除了冯子越派人下狠手,还能有谁。他对跟过自己的女人和自己的孩子都那样,你说他还有人性吗?小薇,你跟着他太危险了,你看你现在这个要死不活的样儿,你别说你爱上他了。”我大声地哭喊着:“我没有,我没有!”艾云紧紧抱着我:“行行行,你没有,别闹腾了。我的祖宗,脸都哭肿了。”
都说借酒消愁愁更愁,也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是不是只有失去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疼才告诉我,傻瓜,你已经陷进去了。就是对那个不该陷进去的人,对那个别人眼中的衣冠禽兽陷进去了。只要一睁眼,就会想起他的一举一动,一个皱眉一个微笑,本来想着开解艾云,最后成了陪艾云喝酒,喝得醉醺醺,她骂林育诚和冯子越,我哭,喝高了就唱,唱的啥自己也不记得了。有次艾云清醒了笑我唱《两只蝴蝶》,难听得能吓死人。我却是完全没印象。我都不记得我还会唱《两只蝴蝶》,真是喝高了。折腾了一个礼拜,终于一天清晨,艾云扯着我到卫生间,把我摁在洗脸池里一盆冷水从头浇了过来,用力给我洗了脸洗了头,扯着我照镜子:“看,赵小薇,这才是干干净净的你,冯子越不是走了吗?正好,你赶紧给我重新好好做人。我要去林育诚老家走一趟,离婚?我让他付出足够的代价再说。”艾云终究是艾云,很快就振作去筹谋下一步了。
艾云走了后,我独自守在她的房子里,却夜夜无法安睡。思念像疯长了的草四溢。我抑制不住,不想一次次地在醉生梦死里慌了自己,却也无法安宁入睡。
忍了三天,最终还是回到冯子越的家,家里没人,保姆也不知道哪去了。我看看我一手布置的书房,想起刚买回那堆廉价的摆件,他倒是饶有兴致,还对我的杰作评论不已;走到他的书房,他生病时我给他买的小龟还在,想起那时对他说,“小龟长寿,讨个彩头。”他皱眉:“总觉得是骂我王八。”说归说,有空他还是会喂喂小龟。现在想想,他皱眉的样子也没那么讨厌;转到厨房,第一次学着熬红豆粥,是因为他把我买的红豆粥全喝了,那时,自己便动了心思了么;来到阳台,荼蘼夏夜,他在这里拥着我感受过习习凉风,再到卧室,我已是泪流满面,哭着滑坐在地上。拿出手机,好想拨出那个在我心里转了千百回的电话,终究还是没能。难别离,究竟是恨还是爱……和他的一幕幕像电影似的从我脑海里闪过,开始的恨,却次第,点点滴滴,不知何时已化作了丝丝缕缕的依恋。
不知不觉,天色已暮,和他分开已经十天了,十天,他没有电话,没有短信,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得一干二净。原来,他真的能做到这么决绝。是我真的让他绝望了吗?还是他本已厌倦了?抑或我只是他的沧海一粟,纵然有些挂怀,在莺莺燕燕的世界里还是很容易把我忘记?脑子里在不停地胡思乱想,好多人的话像潮水一样涌来,小丽的“听说他花得很”,艾云的“他上过的女人比我们见过的都多”,保姆的“我在别家做长期的”,陌生人的“子越,令宜,你们来啦?”……一句句几乎将我淹没,让我窒息到直抽气,全无挣扎的力气。
举报
回复
楼主:文安AS时间:-08-:07:15
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地站了起来,把小龟喂了,小龟似乎饿了好几天,欢快地扑腾着吃。看得我丝丝心疼。小龟,你和我一样都没人会在乎了呢。留恋地又看了房子一眼,我静静地锁上门离去。
去了一次,就像开启了一扇通往他的大门,还想去第二次,第三次,哪怕就是去能感受到他已离去的气息,还是想去。第二天忍不住又去,给自己的理由是小龟饿了需要喂。一路的纠结辗转,却是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程那么快就到了。屋里没有人,保姆可能是被他辞了或者到了其他家吧。我心内暗暗嘲笑自己,人家也许已经转移阵地了呢。喂了小龟,静静坐到窗台前的椅子上,看着楼下,不知过了多久,遛狗的女人多了起来,楼下的人来来往往多了起来,我才惊觉时间又不早了,日已西陲,正要起身,忽然心猛地一揪,开始突突地狂跳,他的车。正慢慢地从楼前开过,从这里可以快捷地通到地下车库,然后电梯上楼。我一惊,就有种想夺门而逃的感觉,却发现他的车并没有继续往前走,而是在楼下停下,他走了出来,我的心像要跳出来一样,紧张得竟然两手都是汗,看不清他的神态,只见一身正装,他很喜欢穿深色的西装,显得很冷峻。他要上来吗?我几乎有些站立不稳,手紧紧抓着阳台的栏杆,却见他靠在车上,点燃一支烟抽着,看着楼上我这里房间的位置,我一惊,赶紧躲在了阳台的窗帘后面。我在窗里看着他,丝丝心颤,他在窗外看着这里,应该看不见我吧,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是路过来歇歇?还是他看见了我不想上来?
就这么对看着,很像卞之琳的意境: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子越,不知道这几夜谁在装饰你的梦,我的梦里,全是你啊……
一支烟的工夫,竟然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起初不经意的你,和不经事的我,经历了这些,究竟你是什么心情?我好痛,几乎支持不住,扯着窗帘缓缓地蹲了下去,眼泪早已不自觉地滑落。他抽完烟转身上车离去了,我从窗帘后走出来,伸出手,却是玻璃窗隔在我的面前,抓也抓不到什么。
隔了几天,接到了邵琦的电话,说她家周末要开个小型Party,问我要不要去。对这些本就没有兴趣,现在又和子越分开了,更不适合去那个圈子里了。虽然真的很想再见见那个美丽的瓷娃娃。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身体不舒服”。可邵琦在那边糯糯的声音:“姐姐,你来嘛,好久都没有见你了。”我迟疑了一下,说:“我现在住在朋友家。”希望邵琦能明白我的意思,住在朋友家就是和子越已经分开了,不再适合和她们一起了。邵琦“哦”了一声,转而特别诚恳地说:“姐姐,可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啊,你来吧,我让徐硕去接你。”我心一暖,再也无力拒绝。
傍晚时,有个陌生的号码打来问我住哪里,便是徐硕了,只是听着声音似乎有几分耳熟。待见到了,我一愣:“是你。”他微微一笑:“我可早知道是你了,小薇。”原来徐硕就是上次子越带我去参加宴会的老徐总的儿子小徐。有了认识的人,我心里稍稍平定了些。一路闲聊,我好奇:“你和邵琦很熟还是和周川?”徐硕的声音淡淡的:“我和邵琦是大学同学,和周川从小就认识。”我更有些惊讶了,笑:“看来你成绩也不错嘛。”邵琦那个学校分数并不低,除非是特招。徐硕也笑笑:“我看起来很差劲吗?”我忙摇手:“不是,不是那个意思。”说实话,以前我总以为有钱人的孩子差不多都是纨绔子弟,骄横霸气的那种,和子越见过几个后印象有所改观,的确大部分肯定是从小家里宝贝着恨不得天之骄子似的自负,但也有不少家教极好温文有礼的,徐硕尤为特别些,初看来阳光纯净,似乎不染一丝尘埃,上次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这次与他聊了几句,却发现他内在有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成熟细敏,其实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简单。是大家族的历练还是天性使然?我也不好说了。
邵琦是在通州那边一处别墅里,环境倒不像老徐总那里那么奢华,有点欧式田园的感觉。到了邵琦家里,邵琦热情地过来拉着我问长问短,看着她真是由衷地喜欢。我们算是去得早的,邵琦笑着端出一盒点心:“先给你俩尝尝,我现烤的。”我刚尝了一块便由衷赞叹,“好手艺!”却看到徐硕正目含笑意看着邵琦,我的心就是一突,不动声色细看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希望是我多想了。
邵琦在徐硕面前倒是很随意:“徐硕你自己待着,我带小薇姐姐去逛逛。”我也正好想参观参观她这里,便随着她一起,却是直叹大开眼界,好多搭配,她很敢想。我指着一件骷髅头的画像抽嘴角:“这个……是谁的品味?”邵琦淡淡笑笑:“周川的,不过看惯了,我也喜欢了。”这都能爱屋及乌吗?我心里直抽搐,我看这玩意儿看一辈子也喜欢不了。
忽然我心一抽,“邵琦,我想看看令宜的照片。”邵琦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两眼,咬咬嘴唇,“真想看?”我点点头。邵琦带我到她卧室,电脑还开着,她点开一个文件夹,“这是去年在一个酒会上拍的。”
我只看了一眼,便有些眩晕,令宜,这便是别人口中的令宜,美得让人震撼。她挽着子越的胳膊站在一起,看着是那么优雅的一个女子。二十多岁,黑色的礼服衬托得她腰肢婉转,看着很高挑,几乎和子越一般高,头发挽着,白皙的脖颈像天鹅般,难得的是她的神情,自内而外的一种优雅,甚至可以说是高贵,这是我极少见到的一种气质。子越的表情呢,似乎在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话,没有看镜头。咔嚓,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裂开的声音。原来,他的身边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女人,相比起她,我就像玫瑰旁边一株不起眼的狗尾草。瞬间便自惭形秽了。
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汉武帝的两个夫人,邢夫人和尹夫人,都很受武帝的宠爱。但是却一直不得相见。一日尹夫人提出想见见邢夫人,武帝和她开了个玩笑,让别人穿着邢夫人的衣服来见,尹夫人一看便说这绝不是邢夫人。武帝惊讶,让真正的邢夫人出来相见,尹夫人一见便说:“这才是真正的人主啊!”说完痛哭不止。当年在大学图书馆看到这一段觉得十分好玩,还暗暗笑古人就是夸张,这有什么哭的?而今却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滋味,当你心里有了一个男人,渴望在他心里有那么哪怕一寸的位置,让他在午夜低回的时候,在四下宁静的时候,起码能嗅到你淡淡的香气,但是你发现有一种美艳的花已经在他心里长满了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卑微、渺小,没有自己生存的一丝夹缝,似乎被人连根拔起,一切都是那么微不足道的惭愧。
我的眼眶也不由湿润了,为了掩饰,笑笑:“真美。”邵琦叹气:“所以她才是不倒翁啊。”我一愣:“不倒翁?”邵琦说:“是啊,冯总身边的人形形色色地换,但每次重要的酒会,带的肯定是她。她很会应酬。”我的心有种被剥得血淋淋的感觉,从头到脚麻了下来。她才是他身边的女人,出得厅堂能为他撑门面的女人,我算什么?又渺小,又怯懦,又倔强,也不可爱。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面对着令宜的照片,我几乎想落荒而逃,她的笑容让我有种撕心裂肺的自卑。
察觉到我的僵直,邵琦回过神来:“姐姐,我们不说这些,快下去吧,客人该来了。”说着用力扯着我下了楼。
可我却像失魂落魄了似的,半天提不起精神,走到客厅的时候,脚一软差点摔倒,徐硕一把扶起我,笑问:“邵琦给你看什么惊悚的了?吓掉魂了似的。”我只能勉强地笑着,凄惶地看着他。他不觉也是一愣。
客人三三两两的来了,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左右的年轻人,人也不多,共四对儿,我才明白邵琦非拉上我的目的,这里只有徐硕在落单,别人不管是朋友还是什么都会带个伴儿来。有人开玩笑:“男主人哪儿去了?”
邵琦抿嘴笑:“待会就到。”正说着,一个洪亮的男声响起:“谁说我呢?”门口出现了两个男人,一个高而壮,一个高瘦。高壮的先用力拍拍高瘦的男人的肩膀,说:“我弟弟,周亦。”算是给大家做了介绍。
第一次见到周川,周川的造型很像个艺术家,头发卷着,不知道是烫了还是自然卷,下巴留着一撮小胡子,看着很Man,也很帅,有点艺术范,也不过分夸张,和娇小精致的邵琦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周亦很瘦,看着文质彬彬弱不禁风似的,皮肤有点黑。
周川大大咧咧扫视了一圈,冲大家都点点头,看见我有些迟疑,徐硕冲他笑笑:“赵小薇。”我一愣,皱皱眉头,这种感觉似乎我与他有什么似的。但也不好辩驳什么,只好冲周川点点头微笑。周川回了个夸张的了然表情,极为搞怪,我忍不住“扑”的一笑。可能大家都习惯他搞怪了,我的笑声有些突兀,便脸红了。
周川随意和大家聊了一会儿,开始了开场白。原来这个Party是为他弟弟周亦接风洗尘的。周川之所以来得晚,就是去机场接他弟弟。有钱人似乎都会去国外镀镀金,周亦也不例外,据说是从法国回来的,学的金融,此次回来是帮助周川料理北京公司的业务。其他的人纷纷极力赞叹周亦年轻有为,青年才俊。我却深不以为然,大学时也有些同学毕业了家里送出国的,门槛极低,学几个月的语言便能出去。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自助的晚餐结束后,周川说叫了几个朋友助兴演几场。待表演的人来了,我才吃了一惊,原来是一个近来很火的组合,能引来无数少女尖叫。我才意识到周川的能量也不小,一个小小的家庭聚会,都能找来这个组合助兴。
所以说什么是有钱人呢,除了花钱一掷千金外,似乎还有很多丝丝蔓蔓的牵连,像上次老徐总的字画是某政府官员送的,他们的社会关系似乎如流水般,无孔不入,政界,商界,文艺界,都牵绊在一起,牵一发全身皆动。
子越呢,他也会是这样无孔不入的人吗?他自然是,之前也陪同他出席过一些场合,他是交际很强的人,他的交际灵活睿智,我听来的感觉常常像是不带硝烟的战争,而且他的手段似乎也是花样百出。想到这些,我不禁又自惭形秽了。我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子越的世界。我只能在一个简单的房间里做些简单的饭菜等着他,无法像令宜一样陪他周旋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场,做他的不倒翁。心开始酸,手中的酒便把持不住,一杯接一杯地灌了进去。以前我是远离酒的,不知从何时起,心痛的时候,便只有酒能做我的镇痛剂。
一个身影来到我面前:“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去玩玩?”我一看是周亦,也没吭声笑笑,抬起惺忪的眼睛,乐队已经在放节奏感很强的DJ音乐了,客厅里早腾出舞池空地,大家正在随音乐摇摆着,都是年轻人,很容易就热闹起来。
忽然乐队的节奏更快,周围的人渐渐停了下来,只有中间的一人正在表演街舞,动作腾空翻越着,非常精彩。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你男朋友跳得不错。”周亦赞叹。我一愣,仔细看看,哦,跳的那个人居然是徐硕,真没想到他还会这个。我有气无力地说:“他不是我男朋友,我是邵琦的朋友。”周亦一愣,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这个聚会虽然是为周亦办的,但是周川却是绝对的核心。周亦只是在介绍之后,便将主场让给了周川,周川说话嗓门很大,而且喜欢搞怪开玩笑,这会儿正在敲着架子鼓,我虽然不太懂,但是节奏听起来很顺畅,有的跟着也在摇摆嬉笑着。邵琦坐在一边,满脸崇拜神色地看着周川,仿佛周川是她心中的男神。看得我的心一阵酸,邵琦的男神是周川,可周川呢?心里能有邵琦的多少位置?我不了解周川,他爱邵琦吗?他只是在专心地敲着架子鼓,偶尔抬头和他的兄弟朋友做个努嘴蹙眉的搞怪表情,似乎他们才是个整体,完全没有和邵琦的眼神交流,也不去看邵琦深情凝视的目光。如果说周川很爱邵琦,起码目前我不信。不过转念又笑自己傻了,这么久了,还有这种念头,什么是有钱人的爱情?相濡以沫心心相印不是有钱人的爱情,他们不会和你吃一碗拉面把里面的肉片让给你,他们也不会在你累的时候给你捶腿揉腰捏肩膀。也许是没到了那一步,但是即使到了那一步也极少有人能做到。因为他们习惯了他们眼中的女人就只是“女人”这种物品。无法当作平等的交流对象而彼此理解,彼此尊重,无法把你当作橡树身边的木棉,一起撑起风雨。这种感觉,怕就是做有钱人的“女人”的代价。
徐硕在和几个朋友开心地聊着,我看着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个局外人,只一杯一杯地喝着酒,开始只是无聊,喝多了心里开始不痛快,而酒做着我的镇痛剂。周亦在我身边坐着,拿着一小杯红酒抿着,笑:“你喝得不少。”我也是喝多了,说话也大胆起来:“你是主人,怎么能嫌客人喝得多。”“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周亦有些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脸憋得通红。“扑哧”我笑出声来。笑声被喧闹的音乐掩盖得不露痕迹。看他似乎也蛮无聊的,我提议:“不如我们两个去那边一起喝。”我指着客厅南边阳台那里的两张摇椅,应该是平时看风景用的。“好!”周亦答应得爽快。
这里稍微清静些,起码说话不用扯着嗓子喊了。但是清静了,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两个陌生人,坐在一个陌生的角落,该说什么呢。我也无心与他闲聊,只是想喝酒,而在这种喧闹的场合,自己独自喝酒似乎又太孤寂,也许就是我拽着他过来的原因。他倒是似乎有很多话,拿着酒杯一直在来回旋着杯口,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忍不住问:“心事很多啊?”“不是。”他立即答,挠挠头说:“只是不知道和女孩子聊什么,又怕说错了。”俗话说酒壮怂人胆,我那天一定是被壮了,也许是酒精,也许是在腼腆的男生面前我会放松些,我忍不住笑:“那你在你女朋友面前也这么吭吭哧哧说话啊?”他眸子一黯:“我们分手了。”我一愣,觉得自己问的鲁莽了,忙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没什么,也不是秘密。回国前分的。”周亦大大喝了一口,淡淡笑:“她的确是嫌我不会说话。”我本是有些好奇,看着说话挺流利的啊,还能把女朋友惹毛是怎么种不会说话法,但毕竟刚认识,也没好意思张口。便抬起手:“干杯,都会过去的。”一杯又一杯,也不知喝了多少,后面的事情已经没印象了。
我心里一紧,慌忙看身边的衣服,还好,是整齐的和衣而睡,心微微踏实下来,头疼得要命,暗暗骂自己越来越不像话了,从前不能说滴酒不沾,也绝不会这么没分寸,竟喝到人事不省。坐起来,看到床边的书桌上趴着个人,还在睡着。我下了床,整理好衣服,使劲咳嗽了两声。那人被惊醒了,迷迷糊糊站起来,揉着眼睛和我说:“醒了?”是周亦,我略微有几分不悦,这是个别墅,又不是个小公寓,房间多的是,干吗非趴在我这里。也不好绷着脸,只好淡淡地应了声,便也不看他,就走了出去。
邵琦已经在楼下忙乎了,正在向餐桌上摆早餐,见我下楼,笑吟吟:“姐姐,你起来啦。”我扫扫四周:“你的周川呢?”邵琦叹口气:“昨晚又和那帮朋友出去了,还没回来。”我顾不上搭理周川的事情,皱眉,拉着她小声说:“你糊涂啦,怎么让我和周亦一个屋子啊,说出去多难听。”邵琦抿着嘴一个劲地笑,笑得我心里直发毛,上下把自己打量个遍:“你笑什么?”邵琦摇摇头,笑着:“姐姐,你昨晚喝多了,扯着周亦的胳膊不放,我怎么拽都拽不开。”“啊?”我不禁掩口惊呼一声,我也太没劲了,酒量不好就不说了,酒品还这么差,顿时羞得面红耳赤,不禁小声问:“我还干什么了?”邵琦已经笑得捂着肚子直弯腰了,看着她笑我更发毛,“快说啊”,我催促着。
“姐姐……”邵琦笑着,“姐姐拉着周亦,一个劲的嘟囔,不要走,不要离开我……搞得周亦面红耳赤,我们要把你拉开,你拽得紧紧的,最后周亦把你抱上了楼,大概怕你半夜醒来喝水,就没走……”如果说用漫画形容我当时的表情,那一定是满脸灰白,头上天雷滚滚的样子。我抽着冷气,怯怯地看着邵琦:“都谁看见了?”邵琦咬咬嘴唇,憋着笑:“不多,都看见了。”我又一次感觉到头顶一声炸雷劈过,再也说不出话。邵琦扑哧一声:“我逗你的,就我和周川周亦,那帮朋友先出去开车了。”“你太坏了。”我追着邵琦就打,却看到从楼梯上下来的周亦,不觉脸红了,有些不好意思。周亦倒是表情很坦然,冲着邵琦说:“有没有牛奶啊?昨晚酒喝多了,胃不舒服。”说完看着我笑笑:“你也喝点。”邵琦促狭地冲我直乐。我想如果目光可以杀人,我的眼神一定把瓷娃娃割了好几遍。
吃过早饭周亦要送我回去,我忍不住问:“你刚到北京,认得路吗?”周亦笑:“我又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周亦的车是辆路虎,他开得也比较猛,不像子越开车除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飙车,一般还是很稳的。周亦开车喜欢快油急刹。都说车品如人品,看着周亦,稳稳妥妥的样子,却没想到开车和他说话的风格截然不同。一路我不好意思说话,他也没有吭声。快到艾云那里时,才犹豫着问我:“我过两天就要去上班了,你可不可以带我逛两天北京?”我一愣,“你不是来过北京吗?”周亦不好意思地说:“来过很多次,也住了很久,但是从没出去逛过。”我有些为难:“那些娱乐场所我也不熟啊。”周亦咧嘴笑了:“我就不喜欢我哥他们那些地方,太闹,你就带我去逛逛景点公园什么的好吗?”我的下巴险些掉下来,我没听错吧,一个开着路虎的公子哥,让我带他去逛北京的景点,我抽抽嘴角:“是北海、长城、颐和园吗?”周亦的眸子有了神采:“对,就这些地方。”周亦的脸庞在晨光里,洋溢着一种恬淡的光芒,我险些就把他认为是我的高中同学,来北京要我带着去逛景点。这个亲民简单的要求瞬间把我和他拉近了许多,我点点头,认真地说:“好。”
我从没有想到,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也来过北京很多趟,居然没有去过普通人来京必去的景点,而且还甚有兴致。当我答应后,本已到了艾云楼下的路虎急速调了个头,向着二环路的方向奔去。还真是急性子。
好在我对北京的名胜古迹虽不狂热,也还有几分兴趣。古典和历史对每个女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吸引力吧,面对红墙黄瓦的深宫宅院,也难免会暗暗揣测里面上演过多少幕步步惊心。
和周亦在一起的最大好处是,他有些腼腆,因此不会有和其他有钱人在一起的压迫感,说话也随意了很多。闲聊着问起:“为什么来北京这么多次都没去这些景点儿啊?”周亦无奈答:“我哥总喜欢拽我去他那个圈子。他们怎么会来这些地方。”“自己来嘛。”我忍住了后半句,也不是小孩子了,干吗还总的哥哥陪着。
“自己,怪孤单的。”周亦嘿嘿笑了两声。我心里一震,有丝说不出的滋味。有钱有有钱的负累。就如你穿得西装笔挺,是决然无法享受小摊上的麻辣烫,纵然口水溢出,也只能暗暗忍着。周亦恐怕就是那个可怜的望着麻辣烫的人。对他不免又有几分同情。
第一站先到了雍和宫。我对雍和宫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原来是雍亲王胤禛的府邸,后就将这里作为西藏达赖班禅的行宫,类似驻京办那个意思。而且现在香火很旺。记得大学舍友姐姐求签证前,一惯要睡到自然醒的她居然凌晨五点就闹钟起来,森森地去水房洗脸。我实在好奇问其缘由,告诉我要清早沐浴斋戒,去雍和宫求签。雍和宫求签证很灵。我当时很惊诧她还信这个,但她中午欢呼雀跃的神色还是让我对雍和宫莫名地产生了几分敬畏。
到了门口我问他要不要导游,他一口说不用。我怯怯地说:“不请导游,我可不会讲。”周亦摸摸头笑:“我给你讲。”我本以为他只是个玩笑,但是一踏入雍和宫的大门,我可知道他真不是客气。从房屋是硬山式还是歇山式顶,到屋脊上的神兽都是什么等级,叫骑凤仙人、龙、凤、獬豸、行什,等等;从雍和宫原是胤禛府邸乾隆就在这里出生讲到雍和宫的罗汉菜。几乎每个物件都能引发他的长篇大论,这个时候的周亦,一扫腼腆害羞的模样,到有点儿像百家讲坛上的袁腾飞,口若悬河滔滔不止。看得我一愣一愣。
我想考考他,便随手指着屋顶上横着的脊梁,两边是两个兽头,问道:“那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是想考周亦,倒也是我一直的疑问,每次和同学来人家问,我都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但是回去又懒得去查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会周而复始地让自己陷入张口结舌的境地。
他又开始滔滔不绝:“那叫鸱吻,是龙之九子之一。传说龙王死后,两个儿子争夺王位,谁都不肯相让,最后决定比赛定胜负,看谁能将一条屋脊吞下去,老大的武艺不如老二,便趁着老二吞屋脊的时候,用一把剑将老二钉在了屋脊上,你看那鸱吻背上,是不是有把剑?”我仔细看去,似乎还真有。以前从来没注意过,我有点激动,指着笑道:“我看见了,哈哈,以后我可以在我们同学面前卖弄了。”周亦却是神色一黯,淡淡笑道:“所以,鸱吻又叫吞脊兽。”说完似乎意犹未尽,仍在盯着屋脊看着。
点击↓↓「阅读原文」让帅哥美女尖叫的地方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颠病初期症状你我携手共抗白癜风转载请注明:http://www.haikuoyua.com/ymjt/12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