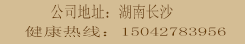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形状 >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形状 >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形状 >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形状 >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宋朝知识分子的十种死法
又名:知识分子的幸福
文/司马少
人们谈论宋朝知识分子的幸福,必然要说两件事:一是有钱花,随便花。二是不能杀,不会杀。
一
有钱花,指的是俸禄高。
宋朝官俸为历代最高,这一点没有争议。不过这说的是,宰相、枢密使、节度使这种顶级官员的俸禄非常之高,换算下来,月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十万元。
但,众所周知,历朝历代,官做到宰相这个级别,收入来源早就不重要了。
你看北魏——就是姓拓跋的那一家,他们家有个孝文帝改革,每个中学生都要背的——北魏初年,官员根本没有俸禄,也没见饿死几个呀。那时候,人家讲究的是官商勾结合作。一旦得到官职任命,就马上去找大商人谈投资。官不一定能做大,但融个天使轮还是没问题的。
古代官俸的多少,往往根据官阶的高低,呈几何级递减。比如清朝,亲王年俸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一品官是一百八十两,到七品县令,就只剩下区区四十五两了。
宋朝宰相、枢密使,月俸是三百贯,另有禄粟(粮食)一百石,带侍中、节度使、宣徽使等加衔者,月俸是四百贯,禄粟二百石。春、冬两季,又有绫、罗、绢、棉等衣赐,算下来也值二三百贯。此外还有茶、酒、薪、炭、盐等诸多补贴,又有官派的侍从,七十人至一百人不等,且侍从的衣粮也由朝廷供给。官做到这个级别,真个是有钱花,随便花。
然而降到团练副使这一级时,月俸就只有二十贯了。当时,高级官员被发配到远恶州郡去做团练副使,是常有的事。我们知道,大文豪苏轼,就曾做过团练副使,他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写成的。
为了避免直接饿死,当时文豪已经主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在山坡上开垦了十亩荒地,又亲手搭建了几间农舍,取名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做完这些,他高兴地写诗说:“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大概到黄州之前,是这样的:
小白脸潇洒自在状。
到黄州之后,就这样了:
大黑面生计堪忧状。
《后赤壁赋》里曾经感叹:“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看起来生活并不富足,即使是在自己动手之后。
二
宋朝依据人口的多寡,将地方各县,分为五个等级。一个万户大县,县令月俸与团练副使一样,是二十贯。而最低一级(不满三千户)的县令,月俸只有十贯,县里的主簿与县尉,则只有六贯。
苏轼身为团练副使,已穷到需要亲手种地的地步。这些小县的县令、县尉们,又该如何活下去呢?
仁宗皇帝刚即位时,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他细心地注意到,地方小官老有贪污的毛病,便问宰相,莫非是俸禄太少,以至于不贪竟活不下去吗?(“岂禄薄不足自养邪?”)
当时身为宰相,月入五十万的王钦若,自己不饿就不管人家肚饥,他给少年皇帝解释说:
“俸虽薄,廉士固亦自守。”
首先承认小官俸禄确实不多。同时强调,做官最重要的是品行,为皇上办差,怎么能谈钱呢。这些没廉耻的家伙,只因坏透了肠子,倒不是填不饱肚子。
皇上一听,心里有谱了,不就是从严治党吗,办!
那个无意间被抓为反面典型的倒霉蛋,叫做郑宗谔,是个小小县尉,月俸六贯。因贪污被判死刑,侥幸遇赦,改判革职。皇上一时好奇,随口一问,被王钦若补了一刀。于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先被打了一顿脊杖,再在脸上刺字,然后发配到安州牢城去充军了。从此他就成了一名《水浒》里常见的“贼配军”。
你大概要问,县尉不是管治安的吗?与知识分子有什么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宋史》记载,元丰三年()五月,进士刘堂,就“如何有效剿匪”这一课题,向皇上进呈了一部《制盗十策》,皇上很高兴,特封其为萧县县尉,以示嘉奖。
你看,当个县尉进山剿匪,也得是进士出身才行呢。(北宋一朝,县尉皆由文官充任,小县不设主簿,便由县尉兼任。南宋初年,仗打得不可开交,才偶有用武官充任边境县尉的情况。)
一贯,是一千个钱。以米价折算,北宋一千钱,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一千二百块。六贯,就是七千二百块。
这样算起来,好像也不低了。
可惜实际到手的钱,却与这账目差着老大一截。
首先,宋代钱贯,有所谓“省陌”,官方规定,以七十七文为一百文,也就是说,一贯钱,实际只有七百七十个。
而发放俸禄时,往往还要打折,一贯钱,实际只给六百,或四百(京官给的多,外任给得少,仿佛是预设外任贪污更容易)。
这还没完,打完折所得到的数目,还只给三分之一现钱,剩下的就以各种物品折抵,什么两百优惠券满八千可用之类的。(北宋初年,州县官俸,一律只发东西不发钱。)
用来折抵俸禄的物品,官方定价又总是比市价高出数倍,明明是两百的优惠券,非要你写张一千的收条。
所以,当时的地方小官,不贪是真活不下去。
后来朝廷也屡发诏书,对地方小官常常领不到俸禄,偶然一贪,又不幸被抓为反面典型而表示同情,要求各地发放俸禄时,至少保证发三分之一现钱。你这全发优惠券,叫人怎么活?
三
也就是说,坊间流传的,宋朝官俸高到让知识分子“有钱花,随便花”的说法,只是后人的一种幻觉。
宋朝官俸,官阶超级高,则俸禄也超级高,比如一旦当上宰相,就肯定不止一个头衔,甚至还封有爵位,俸禄则一路叠加,这种情形,叫做锦上添花。而官阶非常低,则俸禄几乎忽略不计,比如有一个叫“进义副尉”的官职,月俸只有一贯,还三分之二是发优惠券,这种情形,叫做雪上加霜。
所以,就收入这一点来说,我想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幸福指数应该是差不多的。宋朝并没有特别的与众不同。毕竟你穿越过去,不一定就做宰相,也可能是候补的贼配军呢。
四
那么,宋朝知识分子的幸福,就只剩下一个“不杀”了。
以“不杀”为幸福,总不免让人瘆得慌。说明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自由,默认知识分子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讨生活的,偶然看见一个朝代居然不杀,便异常兴奋,有点久吸雾霾忽见蓝天的恍惚。
好吧,这些姑且不论,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宋朝到底杀还是不杀。
五
传说宋朝家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
徽宗时,有一位谏官任伯雨,曾上书劝徽宗赶紧从重处罚奸臣章惇,说:
伏望陛下躬揽之初,先正惇罪。虽用祖宗之意,不杀大臣,而流窜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断,以协公议,天下幸甚。(见《历代名臣奏议》。)
就是说,连处罚罪大恶极的奸臣,也只主张贬,而不主张杀,因为“祖宗之意,不杀大臣”。
《宋史·曹勋传》记载,当年徽宗皇帝被金国人抓去,曹勋随行。后来徽宗命曹勋逃回南边,传话给康王赵构,令其正式即位,扫清中原,来救自己。曹勋临行之时,徽宗传下一句祖训:
艺祖(即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后来曹勋顺利逃回,将话传给了康王赵构,也就是南宋第一任皇帝——高宗。从此,这条誓约就算是公开了。
南宋文人笔记,如王明清的《挥麈(zhǔ)录》,俞德邻的《佩韦斋辑闻》,以及署名陆游的《避暑漫抄》,都详细记载了誓约的内容。后世文人,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宋论》,对此更是乐于称道。
传到现在,则有袁腾飞老师说的,宋朝人只要读书就没有死罪,贪污也无罪释放。
总之是越传越邪乎。现在网上基本认定,宋朝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你想啊,朝廷除了按月给你大量发钱,就什么也不管你了,能不幸福吗?
六
从文献记载来看,宋朝确有“不杀大臣”的祖训。
不过“大臣”两个字,在古代有特别含义,指的是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之类的高级官员。并非念了两句书,考上进士,做了一个县令、县尉、团练副使什么的,就叫大臣了。
所以,“不杀大臣”与“不杀读书人”之间,不免有点小小误差。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宋朝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都有些什么样的非正常死法。
七
首先是为大臣们量身定做的一种死法——贬死。
“贬死”在《宋史》里是一个很常见的词。其意是指,大臣被贬到环境恶劣的偏远州郡,死在路上,或死在任所。
宋仁宗明道二年(),太后病重,大赦天下,明确提到“乾兴(真宗年号,年)以来,贬死者复官”。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又明确提到“取具贬死臣僚姓名,议加恩典”。说明“贬死”是官方承认的一种死法,而且人数不少。
举几个例子吧:
寇准,北宋名相。敢犯颜直谏,宋太宗将他比作魏征。深受信任,太宗晚年连择立太子这样的大事,都来咨询他。宋真宗时,做宰相。其时辽国南侵,群臣多主张迁都,寇准力主一战,最终在战胜的情况下,因真宗求和心切,与辽国订立了和平条约——澶渊之盟。晚年被贬死在岭南雷州。
曹利用,曾北入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南到岭外,平定岭南之叛。是一位功臣。官做到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后来被抄家,贬到房州。路上由一个宦官押送。走到襄阳,这宦官以言语羞辱他,且激且逼,意在让他自尽。曹利用素性刚强,受不得辱,自缢而死。《宋史》说他“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范祖禹,曾与司马光一同修撰《资治通鉴》,负责唐朝部分,前后共十五年。宋哲宗时,一面参与修撰《神宗实录》,一面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苏轼说他的讲课水准,是当时讲官第一。后来因为反对新政,被人举报,说他修撰的《神宗实录》里有诋毁神宗的话。于是在短时间内,一贬再贬,先贬到湖南永州,又改到岭南贺州,再改到宾州、化州。老先生经不住折腾,死在路上。
吕大防,宋哲宗时,任宰相。是《神宗实录》的负责人。同样因为反对新政,被人举报所修《实录》诋毁先帝,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循州,死在路上。
上面所举的是一些古今知名的贤臣。不那么知名而被贬死的,还有很多很多。另外,奸臣如章惇、蔡确、蔡京,也同样被贬到了岭南,或死在路上,或死在任所。
这是北宋一朝的贬死,南宋的贬死规模也很可观,限于篇幅,不再多举。
许多人说起宋朝不杀士大夫,往往会强调那时犯罪也只不过是贬官,语气里仿佛说贬官只是小意思。殊不知,风霜瘴疠也可以杀人。就像上面任伯雨说的,这个章惇罪大恶极,虽然祖宗家法不杀大臣,但贬死他也是一样的啊。
当时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就是岭南,也就是今天的两广。假如你生活在宋朝,收到通知说朝廷要公费派你到广州深圳或者东莞去玩一玩,你就知道,这是有人想要弄死你了。
八
神宗熙宁八年(),发生了一件“李逢谋反案”,牵连甚众。
这件案子,说起来,有些荒唐。
几个被坐实谋反大罪的人,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不过是关起门来看了几本禁书而已。
在宋朝,天文星象、图谶、兵法(《孙子》《吴子》等古典兵法除外),都属于禁书,不许私藏偷学。古人相信天象的变化,与国运直接相关,假如你掌握了星象规律,无异于知道了国家在什么时候会出乱子,然后就可以趁势造反了。图谶则是一种对国运做出预言的书。兵法就不用说了,你偷学打仗,不就是为了造反吗?
李逢出身仕宦之家,曾做过一任余姚县主簿。他就很喜欢看一些这样的书。很不幸,被一个叫朱唐的人给举报了。起初官府不肯立案,说是小民诬告,妄图得赏。后来越查越有眉目,就把他抓起来,细细查问。最后问出一个重量级人物——赵世居。
赵世居是太祖曾孙,也喜欢看这些书,与李逢来往甚密,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朝廷派人到赵世居家里抄检,搜出一些《星辰行度图》《攻守图术》之类的书籍,还有一柄名为“钑(sà)龙刀”的宝刀,谋反大罪,就此坐实。
于是将人抓到御史台,派官员好好查。首先是查看搜到的所有书信,凡是与赵世居来往亲密的人,一律抓起来。
办案官员将书信一封封看下去,看得两眼发懵,上书说:这些书信都是寻常往还信件,与他来往亲密的人非常之多,真的要全部抓起来吗?皇上一想,也觉得似有不妥,遂又降诏,凡是与案情有关的就抓起来。
最后的处罚是:
赵世居,赐死。子孙从宗室中除名,交由开封府监禁。妻、女、儿媳、孙女,一律罚为尼姑。
李逢,凌迟处死。李逢之妻因为早已与他断绝关系,减罪一等,罚为尼姑。其子女罚为官奴。正在做官的一个叔叔,一个哥哥,三个侄子,全部免官。其中,哥哥与一个侄子被流放。
翰林祗(zhī)候刘育,凌迟处死。刘育之妻、子,发配到广南,给军士为奴。
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凌迟处死。徐革之妻、子、女、弟,一律罚为官奴,叔叔被流放。
根据《宋史·刑法志》,宋朝的凌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千刀万剐,而是先砍断四肢,再割断喉咙。
除了凌迟,还有些受牵连的人,被处以腰斩。
试将作监主簿张靖,腰斩。
进士李侗,腰斩。
武举进士郝士宣,腰斩。(武举也要考策问,要求精通兵法——这是奉旨学习,所以也是知识分子。)
还有被判绞刑的。
提举崇福宫、兵部员外郎、直昭文馆傅尧俞,因为在做徐州太守时,有人来告李逢谋反,他没有立案,被判处绞刑。后来遇赦,侥幸减死一等。
此外,还有自杀的。
起初有人举报李逢谋反,本路提点刑狱王庭筠,做了一番调查,说并无造反行迹,只是“语涉指斥”“妄说休咎”,处以流放即可。后来李逢等人到底被坐实了谋反大罪,办案官员将王庭筠也一并控告了。这位提刑官,为了避免身遭极刑,只好自缢而死。
九
李逢谋反案,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个冤案。李逢与赵世居,只是看了几本禁书,其他什么也没干。他们所看的禁书中,那本《攻守图术》,还是宋仁宗写的,内容上自然没有什么忌讳,只是依据国法,他们不准看。
这案子的真正起因,是吕惠卿想要整死王安石。
当时有个叫李士宁的方士,以导气养生之术,游谈于公卿之间,自称已有三百岁,能预知他人祸福,与王安石、赵世居等人,交往甚密。
这李士宁先从别处得了一把“钑(sà)龙刀”,又将这刀赠给赵世居,还赠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后来谋反事发,有人说这是反诗,查来查去,尴尬地发现,这两句诗是仁宗皇帝作的,原是写给大臣的挽词。
吕惠卿的算盘是,坐实赵世居谋反,引出李士宁,再牵连到王安石。
无奈王安石虽一时失势,毕竟深得神宗皇帝信赖。当时神宗要治李士宁死罪。王安石知道,一旦李士宁被坐实谋反罪,自己便脱不了干系,于是与皇上当面力争。最终李士宁仅得到流放的惩罚。举报李士宁诱使赵世居谋反的人,反而有罪了。
这故事说明,想杀读书人的,不一定是皇帝,很多时候,是另一帮读书人。
十
当年袁腾飞老师讲说宋朝诸般好处,说只要读书就没有死罪,即使贪污也无罪释放。这是宋朝皇帝所不能认同的。
贪污在宋朝是一项重罪,一旦查实,通常都是死刑。而且不用贪得特别多,就足以构成死刑。
比如,太平兴国三年(),著作佐郎卢佩,仅仅贪污一百九十贯,就被斩首示众了。你可还记得,《水浒传》里,林冲买一把刀就花了一千贯。
每当有重大喜庆,大赦天下,诏书往往还特别强调,谋反、杀人,以及贪污者,不赦。(详见《宋史》诸帝本纪。)
所以,整个宋朝,因贪污而被杀掉的读书人,非常之多,太祖太宗两朝尤其多。
举例如下——
太祖一朝(见《宋史·太祖本纪》):
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殿直成徳钧,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
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殿中侍御史张穆,坐赃弃市。
右拾遗张恂,坐赃弃市。
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
太宗一朝(见《宋史·太宗本纪》):
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劵,弃市。
监海门戍、殿直武裕,坐奸赃,弃市。
监察御史张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钱籴粜,弃市。
殿前承旨王著,坐监资州兵为奸赃,弃市。
监察御史祖吉,坐知晋州日为奸赃,弃市。
弃市,就是菜市口斩首示众。
惩治贪污,除弃市以外,还有别的刑罚,比如绞死与杖死。
宋朝法令,贪污金额达到三十五匹绢帛的价值,就要判绞刑。(有一时期,满十五匹就判绞刑。北宋一匹绢帛的平均估价,约是一千三百钱。三十五匹绢帛,以米价折算成人民币,约是五万五千块。这被杀的,都是清官呐。)
太平兴国三年(),侍御史赵承嗣,负责到郑州征收商业税,“隐没官钱巨万”,被人告发,按照法令应判绞刑。皇上觉得不解恨,特批弃市。一起被判弃市的,还有七个小吏。——这故事说明,宋朝判刑轻重,有时候是看心情的。
太平兴国五年(),阳武县令张希求,贪污官钱二百三十四贯,直接杖死。(二百三十四贯,约合人民币二十多万,不足宰相半个月的工资。)
十一
两宋之际,与金国打仗,朝廷经常被搞得下不来台,这时候就有许多缸,需要有人去顶。
徽宗时,有个辽国人马植,来向宋朝献灭辽之策。策略是,遣使从山东出海,到辽东去与金国结盟,合力灭辽,以便收回五代时丢掉的燕云十六州。徽宗大喜,赐以国姓赵,改名良嗣,就以他为使臣,出使金国。
此后在整个灭辽过程中,赵良嗣一直是使臣,往返六七次,竭心尽力。在金国不愿归还燕州时,据理力争。金国提出,土地归宋,赋税归金,赵良嗣不允。金国又提出,只收取六分之一赋税,赵良嗣还是不允。最后金国只好如约归还燕州。
朝廷很欢喜,给他一路升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延康殿学士、提举上清宫、光禄大夫。
之后不久,金国叛将张觉以平州归降宋朝(张觉原是辽将,先降金,又降宋)。赵良嗣说如果接纳张觉,便是背信弃义,必然得罪金国,将遗患无穷。而朝议以为,土地多一点是一点,欣然接纳了张觉。
赵良嗣主张平州不属于宋,是做了辽奸又要做宋奸,直接被降官五级,发配到郴州。
最后我们都知道,金国一怒之下,把宋朝打了个稀里哗啦。
朝臣一想,这一切祸患,都发端于赵良嗣一人,于是派人到郴州,去将赵良嗣枭首了。
同时,降将张觉也被枭首,人头送往金国。张觉被杀,所有辽国降将,见之心寒,宋朝北方防线,瞬间瓦解。
后来,北宋就亡了。
到了南宋,被拿来顶缸的,则有著名例子张邦昌。坊间传说,两宋三百余年,一共只杀了张邦昌与岳飞两个人。
张邦昌,钦宗时官至宰相。在金兵围困汴京时,曾与康王赵构一同作为人质,入金营议和。
后来汴京城破,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抓。金国要在宋朝原有领土上,另建一个国家,让宋朝百官自己选一个人,来当这个皇帝,前提是不能选赵家人。
最后公推张邦昌来顶这个缸。于是张邦昌被金国册立为皇帝,国号大楚。
金国退兵后,张邦昌便主动退位,将皇位还给了康王赵构。赵构即位后,任命李纲为丞相。李纲坚持说张邦昌犯的是僭逆大罪,非杀不可。
起初高宗赵构还不忍杀他,只是将他贬到长沙。后来金国人看到宋朝居然这么容易就复国了,只好再次起兵南下。高宗慌了,匆匆南逃,顺便传令将张邦昌赐死。
张邦昌收到赐死诏书,怆然徘徊,不忍自尽。无奈传令人再三逼促,只得郁郁登楼,自缢而死。
十二
北宋在将亡未亡之际,有所谓“六贼”,即蔡京、王黼(fǔ)、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miǎn)六人。据说宋朝之所以闹到这步田地,都是这六人惹的祸。所以,钦宗一即位,便将六人逐一处决了。
朱勔以花石纲得宠,属于小人得志。童贯、梁师成、李彦,官虽做得大,却都是阉人,算不得知识分子。(童贯官至太师,爵封郡王;梁师成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后又进封少保;李彦则官至检校太傅。其中梁师成自称苏轼庶子,颇以翰墨为己任,且曾混得一个进士出身,但史书说他“实不能文”。)
蔡京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在做太师之前,还曾做过翰林学士兼侍读,主修国史,其书法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另三人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而王黼在做宰相之前,也同样做过翰林学士兼侍读。这两位算得标准知识分子了。
蔡京是被贬死的,遭贬之时,已经八十岁,死在了路上。大概皇上不大解恨,追杀了他两个儿子。——其长子蔡攸,官至少师,封英国公;次子蔡翛(xiāo),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讲,加封大学士,提举醴泉观。因父亲势败,先被贬到远恶州郡,不久朝廷又派人追至任所,将二人斩杀了。(蔡京的其他儿子,除一人做了驸马,没被流放以外,其余都被发配到远恶州郡了。)
王黼曾企图废掉钦宗的太子之位。后来钦宗即位,自然与他不合。他想进宫向新君道贺,宫门卫士直接一把拦住,说皇上有旨,不想见你。再后来,金兵将至汴京,他便私自携妻、子出逃。钦宗将其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李纲等大臣认为,这样的人,还留着做什么。于是派武士追上去,将他杀死在一个乡民家里。钦宗觉得自己刚即位就杀大臣,有点不好意思,对外只说是被强盗杀了。
十三
奸臣杀完了,该杀功臣了。宋朝功臣被杀,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岳飞。
岳飞虽是武将,而诗词书法俱佳,是个文武全才。其故事,不必细说。其死法,是在狱中被枭首。其罪名,则是曾经说过一句,自己与太祖都是三十岁时封节度使,这叫做“指斥乘舆”。其子岳云,史书说是赐死,实际是在菜市口被斩首的(弃市)。
枭首是弃市与腰斩的威力加强版。弃市与腰斩,是砍完就算了。枭首则还要把头拎去给人看一看,以示不老实就是这下场。这种死法多是用在小民身上。官员被枭首的比较少。
北宋打不过金国,就杀了一串奸臣。南宋打得过金国了,就把那打金国的杀掉。这怎么能说是“不杀大臣”呢。
十四
宋朝家法,除“不杀大臣”外,还有半句是“不杀言事官”。今人常有被删帖的烦恼,听见这半句,以为宋朝言论环境远胜于今。其实,“言者无罪”这种话,哪朝哪代,都不能当真的。宋朝言官,对此颇有体会。
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被任命为言官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才能把官辞掉。因为言官负责舆论导向,而通常只有当皇上与大臣产生利益冲突,或朝廷与百姓产生利益冲突时,才需要他们发言,说话稍一不慎,就要祸及满门。不做好死全家的心理准备,是不方便接这个差的。
刘安世跟老母说,“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辞,当可免”。结果老母劝他应该“捐身以报国恩”。——当个官,搞得跟上刑场似的。史书对这种不怕死的精神,表示了赞扬。
同为言官的邹浩,得到任命时,第一反应也是想要辞掉(“恐贻亲忧,欲固辞”)。他向老母表达了这一想法。老母答说,我儿能报国恩,无愧于公论,留清名于世间,身死又有何恨。史书对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也表示了赞扬。
王安石刚出道时,文章好,名声也好,欧阳修便推荐他做言官。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赶紧辞掉。“以祖母年高辞。”奶奶年纪大了,怕吓着老人家,所以不能做言官。史书对这种怕死的精神,并没有表示谴责。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古人不像今人那么天真。言官是个高危职业,乃是一种常识,即便是在声称“不杀言事官”的宋朝。
刘安世当上言官后,对皇上与满朝大臣来说,基本上是个豌豆射手,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流放岭南的惩罚,后半生一直处于流放状态,周游了当时所有远恶之地,并且大臣两度派人去追杀他。好在他运气与身子骨都还可以,无惧追杀与瘴疠,顽强的活到七十八岁才死。
邹浩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两度遭贬岭南,惹了一身瘴疾,很快就病死了,得年五十二。
十五
哲宗绍圣四年()闰二月,张天悦上书言事。皇上看了大怒,发下一道圣旨,说张天悦所上书,“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让开封府好好审问。最后查出张天悦除了“诋讪先帝,情不可恕”以外,还私藏了一本《景祐福应太一集要》(不知是什么书,看题目,大概与阴阳五行有关,也属禁书一类)。于是张天悦被处死。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引《编年备要》说:“自是妄言者,莫不诛死。”
次年又发生了一件“胡洁己毁谤指斥案”(他说皇上“外信奸回,内耽女宠”,其言“多讪时政”)。大臣们有的要治他死罪,有的为他求情。但史书说,这案子最后不知是如何了结的。根据《编年备要》的说法,大概也处死了吧。
这一时期,举报他人讪谤,是有赏的。大臣曾劝皇上取消奖励,免得官府天天要抓人去砍。皇上则说,既然举报的是实情,岂能不赏。
《宋史·刑法志》说,神宗朝以前,即便十恶重罪,也不曾用过凌迟、腰斩这种极刑,而神宗朝之后,则往往以“口语狂悖”之罪,将人处以凌迟、腰斩了。
南宋初年,秦桧当政,曾大兴文字狱。不但上书言事者,多被贬死、弃市,连平常书信、诗文、家传著作,甚至亭台匾额,偶有一字半句犯忌,也往往被贬死,或直接处死。(《宋史·秦桧传》说,秦桧当政的十九年间,“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罪名“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
十六
前面说起过,宋朝不允许民间私习天文术数。
太祖太宗两朝,曾下诏让各州将所有懂天文术数的人,全都抓起来送到京师,“敢藏匿者,弃市”,告发者,赏钱三十万。相关书籍,也要全部上交官府,敢私藏的话,你懂的。
有一个叫宋惟忠的人,就被自己亲弟弟宋惟吉告发了,最后以“私习天文”罪,弃市。
像诸葛亮这样的,要是生在宋朝,分分钟就被诸葛均给告发了。
后来一共抓了三百五十一人,其中六十八人被选出来供职于司天台,其余都在脸上刺字,流放海岛。(宋朝的流放海岛,通常是流放到登州沙门岛。此岛位于渤海海峡中,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的长山岛。宋朝在这个岛上建了一座监狱,可以容纳三百人。每年源源不断有犯人往里面送,却没有轻易将监狱填满,原因是“至者多死”。当然,犯人无限往里面送,还是会填满的,多余的人应该送往哪里呢?有官员上书说,岭南春州,瘴疠之地,犯人流放至此,十死八九,希望朝廷不要再将犯人流放到这种地方。朝廷一看,很好,原本该流放到沙门岛的人,也可以去春州嘛。这说明,“流放海岛”并不是放你一马的意思。)
十七
宋朝知识分子非正常死亡的情形,大致如上。限于篇幅,每种情形只能撷取二三实例加以概述,无法尽数罗列。
总结起来,上到凌迟,下到自杀,死法多种多样,可以说超过十种,也可以说不足十种,取决于怎样归类。如果笼统地数过去:
自杀。贬死。追杀。赐死。绞杀。杖杀。弃市。腰斩。枭首。凌迟。
则正好十种。
要而言之,生活在宋朝,除了谋反以及看起来想谋反会被杀以外,贪污会被杀,话多会被杀,小官会被杀,大官会被杀,奸臣会被杀,功臣也会被杀,乱写书会被杀,乱翻书也会被杀,甚而至于,会因朋友被杀而被杀。
那并不是一个皇上只负责发钱的朝代。
十八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幸福这件事。
就像前面说过的,以“不杀”为幸福,总不免让人瘆得慌。
事实上,宋朝的相对不杀,完全依赖于皇帝的宽和性格,而不是一个优越的制度。对知识分子来说,这只是幸运,不是幸福。知识分子真正的幸福,在于可以自由地思考。不杀只是底线,不是上限。
以“不杀”为幸福,那讨论的不是活得好不好,而是苟活得好不好。
宋朝在思想文化上,一直比较小家子气,而且越来越小家子气(这个问题,可以另文详述)。生活在这一时期,而感到幸福的人,一定是思维上没有什么追求的人。
苏轼说,“人生识字忧患始”。
他大概是不幸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