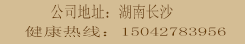非常教师
刘岳,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现担任长沙市政协委员,湖南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系国家“双千计划”学者,中南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年毕业于长沙市第十六中学,年通过公务员招考到长沙市司法局,历任宣传科长、法律服务协调指挥中心主任,年辞职从事社会律师工作。现担任湘一清竹湖实验学校等四十余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
山高海阔忆师恩
----致母校长沙市十六中
一个人的成长总是与家庭和学校紧密相连,家庭是爱的港湾,学校往往是命运的起点。
和很多人不同,我的起点不是大学,而是高中。24年过去,回忆并不都是美好的代名词,在高中,我由“底谷”吃力地爬到“峰顶”,却又遭遇到人生的“滑铁卢”。所幸又是我高中的老师,为我举火燃犀,坚定地陪我跑到中年。
我的初高中六年都在长沙市第十六中学度过。
实话实说,这所学校一度比“四大名校”还有“名”。不过,此名非彼名。十六中地处湖南旅社旁边,自然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初中就近入学,附近不少孩子自带顽劣、油滑的市井基因,把逃学、打群架、抽烟、早恋当做潇洒,以至于还有人把“十六中”称作“十六流”(长沙话把闲散无业人员称做“流子”)。听说是十六中的学生,总有人在背后不住地摇头。
长沙市委、市政府机关与十六中只有一街之隔,一些干部子弟就近到了这里。成绩好一点的,多被父母“拔擢”到了名校去读高中;我这样的,则被沉淀下来,继续被人潮裹挟。
刚进初中时,十二、三岁,这杯白开水,滴啥就成了啥颜色。初一到初二这两年,我成天和狐朋狗友厮混,无心向学。因为打群架、偷单车,差一点还进了少管所。
如此沉沦,哪能考上高中?所幸读初三时,上帝终于为我照进了一缕阳光。
为了吸引前排女生的注意,有一次,我把她的发辫系到了座椅靠背上。她很生气,鄙夷地斥责我:甘心堕落只会让我更瞧你不起!
前排女生并没有料到,她的一番话令我醍醐灌顶,似乎洞穿了我的人生。
那个九月的课间,阳光从梧桐叶的间隙滑落,发出金色的光芒。
那刻起,我变回了真我。我由社会回到课堂,重新拿起了书本。经历一番苦读,考上了十六中的普高。虽然还在这个学校,但以我之前的表现,我早就该分流到社会。能上到高中,这是我抓住的第一根稻草。
那是年。当时十六中高中部是这个样子:巴掌大的操场和两栋三、四层高的教学楼。一些老师调侃,半根烟抽不到就转完了全校。没有红墙绿瓦,没有林荫小道,普普通通的校园,和五光十色的象牙塔相去甚远。
记得十六中当时还办了职高——长沙市旅游职业中专。那时旅游市场方兴未艾,旅游职高“热得烫手”,职高的同学很早就被北上广的高级酒店“预定”。每天,那些俊男靓女和我们出入同一个校园,很早就拿到了高工资。那些,也不能不令年少的我们也曾动心。
十六中的生源显然不能和名校比,两级分化得厉害。不过,班风明显好于初中。特别是,我们感觉到:越是学生不冒尖,学校越是呕着一口气,一直都是举全校之力为高中配备最好的师资。
十六中优秀的高中老师很多,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三位文科老师。今天想来,他们不一定有“特级教师”之类的头衔,但永远是我最恭敬的先生。
政治老师李国华,国之华表,才华横溢。
一般来说,政治课最易枯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类的名词都要记要背,学生往往听得寡淡无味。但在李老师的课堂里,枯燥的名词顿时变身为行走的生命,纷纷穿上了鲜活靓丽的衣裳。不仅如此,他所教的解题方法,在我此后的公务员和律师资格考试中还屡试不爽。
李老师告诉我们,任何作答都有“思路”,依要点立论,按层次展开,就会是一片好文章。例如问题是“为什么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那我们先解释什么叫“生产力”,再解释什么叫“经济基础”,然后分析“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先谈生产力对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再反过来谈生产力对经济基础的破坏性影响,最后论述如何来消除这些影响。
高中毕业后,我再没有接受过任何逻辑训练。后来,我照这套解题方法参加公务员申论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结果每次都得心应手。公务员考试是全市四百人挑两人,律师考试是全省四千人挑一百二十人,我竟然分列第一与第七。
我哪里是什么学霸?用的全是政治课的秘笈(此处偷笑)。现在,谁不抨击几句“应试教育”似乎就显得没文化。殊不知,“考试”本身并没有错。遇到李老师这样的人,不只是当时,就是后来若干年一直都在影响我。怎能不心怀感恩?
历史老师毋南征,十六中的传奇,没有之一。
“毋”姓本来就是北方姓氏,他父亲是南下干部,故为其取名“毋南征”。毋老师一米八几的个头,浓眉大眼,头发乌黑蓬松,脸部棱角分明,用现在的话说,“少女少妇通吃”。标准的“红二代”,又极有才,所以独来独往,素面朝天。不悦其心者视之如无物,半句都是多言。这么说吧,他只穿自己缝制的衣裤,尤喜风衣,戴墨镜,又偏好白色,在整个八、九十年代的十六中校园,唯见他白衣飘飘,俨然行走江湖的侠客。他又好烈酒,而且每酒必醉,醉前又必吟诗,所以我们总把毋老师看做当代李白。杜甫诗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说的就是他。
明明可以拼颜值,但他偏偏要靠才华。
毋老师讲历史,有趣、有种、有料,如果当时就有网络传播,很可能没有袁腾飞什么事。那时候,同学们都扯长了脖子听他的历史课,连最顽皮的孩子都老老实实。快30年过去了,同学聚在一起,几乎没有叫不出他名字的。
上下五千年风云,被他一袖收入怀中,仿佛是“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然而,他并非只在气势上藐视一切。他从不要求死记硬背,也不划重点,而是跳出课本讲典故。兴奋处,手舞足蹈;动情时,潸然泪下;到了考试之前,他又会串起所有知识点,以最通俗好记的方法,帮我们轻松过关。
毋老师对文字的研究十分深入。我喜欢听他在课堂上说文解字,看他拆解汉字的偏旁部首,教我们体会象形、会意等造字方式。他的板书遒劲飘逸,往往一列一列竖着写,抬头便是一整版。
毋老师年轻时正赶上“文革”,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骨子里的“愤青精神”从未褪去。他不照本宣科,他认为课本上有些历史是被颠倒过的(此处略去一万字)。他要求我们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下课铃一响,毋老师从来就是夹起书本就走,头也不回,丢下满班同学,一身白衣地消失在校园尽头(他甚至从不去教研组,也不批改作业,呵呵),这些都为他的孤傲写下了注脚。这样的老师,很早就在我们年轻的基因里埋下了桀骜的种子。
然而,整个高中三年,我最敬爱的还是班主任汪洁老师。
作者和恩师汪洁老师(左)
汪老师是长沙县人,当时刚从汨罗一中调来不久。个子不高,短发,戴眼镜,穿着朴素,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直指人心,别看她教我们时已经四十出头,却十分符合文艺女青年的气质。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做过省一级的巡抚,祖父当过民国时长沙县的县长,叔伯一辈出了不少的高官和教育家。她毕业于北师大。那可是培养教育工作者的最高殿堂啊,但我至今都不知道究竟是何种际遇,才把她“下放”到十六中。
我感谢那份神秘的际遇。
汪老师教我语文。她的语文课,从来就不只是教学生认字、语法和作文,她最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启蒙、美学教育和人生教化。我属于“慢熟型”男生,在汪洁老师的牵引下,初三照进的那一缕光,在高中燃成了火把,并把我由混沌托举到光明。
汪老师当过知青,在农村中学任教多年,她常常讲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讲她如何从一个不习惯农村生活的小姑娘,慢慢扎根于艰苦的环境,和农民以及农民的孩子打成一片,甚至“斗智斗勇”,让顽劣的学生一点点进步提高,直至送他们从乡村走出大山……
她也多次讲起农村的孩子,如何翻山越岭,自带干粮,到学校就读,放学走回家还得干农活;讲起他们如何在四面透风的宿舍,顶着豆大的煤油灯,彻夜苦读,只为考取大学,改变命运……
汪老师是感性的,每次讲到这些,她的眼角会泛起泪花,再背对着我们擦干。
汪老师又是理性的,鼓励我们不要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要摒弃城市的喧哗,把人生的书本看深看透。
汪老师从不因循守旧,她懂我们的心。当时,学校领导担心我们早恋,要求班主任狠揪“反面典型”,汪老师却向我们坦然相告:她给我们讲《少年维特之烦恼》,要求大家克制青春期的情感冲动,把异性同学间暗生的情愫,转化为互帮互学的动力。她激动地说,我不赞同高中生早恋,但我理解人类的一切情感,任何感情都是无罪的!记得她讲完这段话时,同学们先是一片沉寂,然后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现在回想,这才是真正的“人”的教育啊!
汪老师的语文课,真正让我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在她的课上,师生永远是平等的,老师、学生都可以围绕主题,相与疑析,相互探讨。笑声和争论常有,空洞的说教却未曾有过。记得有一次,汪老师给我们讲红楼梦,讲到探春痛打恶妇王善保家的那记耳光,她说,这一记耳光,着实一解胸中闷气,足足响彻了二百年!话音刚落,大家噗嗤一笑。现在想起这个桥段,我甚至会情不自禁摸摸脸,生怕这记耳光是打在自己脸上。渐渐地,我喜欢上了包括语文在内的所有文科。
我这样的孩子,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傲,心灵的枯井一旦被激活,就要迫不及待地掀起浪花。汪老师敏锐地捕捉到我的表现,不断给我激励,把我当做可造之材。在全班,我可能是她谈话次数最多的学生。她还多次到我家家访,和我的父母都成了好朋友。她了解到我父亲也是通过苦读而成才,她又勉励我把父亲当做榜样。
我甚至是通过汪老师,才理解到父亲的伟大。
由于初中时学业荒废,高中时我学得十分吃力。用长沙话讲:麻布袋子绣花—底子差,要勉强赶上趟,得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然而,因为汪老师的鼓舞,我的高中学习极其刻苦。为了提神,我不知抹光了多少瓶风油精。有时熬夜到黎明,看着挂在窗前的朝阳,我甚至产生错觉,以为这是黄昏的落日。
我的成绩每有提高,汪老师就会当着全班同学表扬我,这又为我再次打进鸡血。
那时,班上喜欢由低分到高分来宣布成绩,最差的同学第一个领试卷,最后领的一定是“骄傲的公鸡”。汪老师见证了我的奇迹。由最先几个领试卷的变为最后领的几位,到了高二、高三,我几乎就是在全班同学的艳羡里最后一个上台。最后,还走上了班长、学生会主席的“领导岗位”。
汪老师的“赏识教育”,让我全面实现了“屌丝的逆袭”。
如果顺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我无疑将是十六中的骄傲。
然而,人生没有假设。
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一般的叛逆是抵触父母和老师,消沉厌学,自暴自弃,我恰恰相反,我学习的动力并不是考一个好的大学,而是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既能达到让大家瞩目的高度,又能让大家觉得我不会按规则出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早已是全年纪第一,模拟考试更是把第二名远远甩在身后,汪洁老师鼓励我报考北大、清华。但那个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全身的血液在沸腾,青春的躁动像魔鬼一样折磨着我,我整夜整夜地失眠,焦躁不安,我执拗地决定,要在万众惊讶中转身,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就在高考前两个月,我给汪洁老师留下一封信,并把我最喜欢的两本《唐诗宋词选集》分赠给她和李国华老师。
我对父母甚至都没说一个字,就带着我的吉他,悍然弃学,南下打工。
我在写给汪老师的信中说,严重的失眠折腾着我,我必须换个环境。考上什么大学已不重要,我既然已经证明了自己,再读四年大学也是浪费。恳请老师原谅我,我要在新的环境里,磨砺出全新的自己。
鬼迷心窍也好,鬼使神差也罢,我的弃考在师生中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二天,医院。之后又拔掉针管,和父亲搭上火车到处找我。全校师生更是一片愕然,高考在即,汪老师不可能放下全班同学来找我,她当着全班同学哭成了泪人,哽咽着读完我写给她的信,说她失去了最好的学生,但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汪老师通过父母给我写信,寄来学习资料,坚定地鼓励我重新回到课堂。
24年过去,至今我还保存着汪老师给我的长信(遗憾的是,最后一页在搬家时佚失)。
我是如此珍爱她的文字,以至于不得不长长的援引。因为,这些句子里有汪老师的气息与声音。
流着泪看完你的信,也流着泪在班级读了你的信。心中复杂得无以形容,感激你的诚实,钦佩你的勇气。你不甘平庸,对追求的目标从不放弃,在统考将迫,肯定可以考上大学的时候,你能勇敢地迈步走上自己选择的路,这是我见所未见的举动,我要从心底向你高呼“乌啦!”……
在你对我的尊重之中,我们相互之间了解还太少了。假如你将自己的感受告诉我,说不定,我会含泪将你送别。亦如母亲送儿子出征,亦如朋友送同道远航。希望绝不只在昨日,也决不只在今天,这我很清楚。
还记得么,我说过:“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你不会逃避,你的离开只是为调适,只是为了找寻,只是为了证明生命和生存的价值。我信赖你!”
……你正走向成熟,虽然你的一只脚还滞留在好奇的年龄(不管你承不承认),你能够独立思考并作出决定。虽然你的思考毕竟大多来自自身的感受。所以作为老师——其实,我更愿意作为你的朋友,我没有权力阻止你。先从实践中学习,这是西方大多数年轻人所走的路,也应当成为中国的青年学生所走的路。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东西方的体制不同,实践而后再学习理论,机会就不那么容易获得。而且说句你不喜欢的话,当今中国社会的实践比起西方来,到底达不得高层次。而当今学府里的理论教授,已打破固思,要比实践得层次高得多。人类的历史,总是在继承前辈的经验,汲取前辈的教训的路上前进的。任何个人,任何时代的实践,都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否则,我们就要茹毛饮血,钻燧取火做起。——这是任何一个小孩都会耻笑的事。所以,历史决定,所有的人,必须向书本学习:承光启后,继往开来。
为了你的身心健康,我赞成你先工作,调适自己的精神,因为一旦崩溃,就会毁了一生。我们的生活中会少一个有大出息的青年。为了其他,我却希望你考虑一下,仍然参加统考”。(信件原件见下图)
高考面前,每个人都奋力冲刺,挺胸撞线,唯独我从线前弯腰钻过。父母的苦劝没有奏效,最终还是汪老师的长信说服了我。
我仅仅是在高考前的一天回长沙参考,甚至连准考证都没脸自己去领。为时已晚,关键阶段的两个月,我的大脑完全处在“高烧不退”的状态,我用高强度的劳动麻木自己,没有看过一页书。
最终,我等来的是长沙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瞟了一眼,放弃了这个公费指标。
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在我们那个“一卷定终身”的年代,高考一脚踏空,后果可想而知。
终于,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惊讶”,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此后的无数个夜晚,我都在冰冷的工地仰望星空,用冲动咽下苦果。
汪老师依旧没有放弃过对我的拯救。
她鼓励我“天生我才必有用”,决不要为暂时的挫折灰心。她建议我参加自学考试,边工作边学习,再寻找机会突破。
我听从了汪老师的建议,在全部同学跨入大学后,我悄悄地回到长沙,一个人找工作,坚持读自考。
自18岁起,我开始了与社会的博弈、融合,摆过地摊、做过搬运,卖过矿泉水,在公交车上干过推销……烈日和暴风雨下,无论多苦多累,我始终像汪老师要求的那样,时刻不忘记自己的跌倒,把学习摆在第一位。
几年后,我考取了公务员和律师资格,从结婚、生子,读本科和硕士,再到后来从机关辞职做律师,人生的每一个关头,我都及时向汪老师汇报,向她报告我的快乐与苦恼,也得到了汪老师的教益。
我把汪老师写给我的信装裱在镜框里,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抬头凝视,汲取精神动力。毕业这么多年,我每年春节依然会携妻小登门拜访汪老师,邀请我的恩师们聚会。
高考的“滑铁卢”让我的命运飞流直下,我至今仍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耿耿于怀,也为年轻时的孟浪深深懊悔,但我从来都是遵从恩师的教诲,从未停止过努力。
我的正规教育止步于高中,是几位恩师对我的性格和人生观产生了关键影响,我的举手投足都投射了他们的影子,他们的教诲跟随我半生,促成了我人生的“拨乱反正”,激励我步步攀登。
当年教我的老师们都已是七十开外吧?他们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我也到了戴老花镜的年纪,身后跟随了一批学生和弟子,我愿像当年我的恩师教导我的那样,用正直无私和诲人不倦去引导和影响他们,完成薪火相传的使命。
师恩似海,岁月如歌。
谢谢长沙市十六中,您永远是我的母校!
谢谢我生命中的恩师,您永远是我的先生。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haikuoyua.com/ymzz/13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