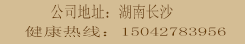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天敌 > 9月19日秋雨连绵每周历史文摘第四期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天敌 > 9月19日秋雨连绵每周历史文摘第四期

![]()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天敌 > 9月19日秋雨连绵每周历史文摘第四期
当前位置: 海蛞蝓 > 海蛞蝓的天敌 > 9月19日秋雨连绵每周历史文摘第四期
要求:认真阅读,做好阅读笔记,并写字左右的读后感。
一、答疑解惑
1、问:公元前年周平王迁都到洛,我记得以前学习历史的时候一直是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我们现在跟学生说洛好呢还是洛邑更好些?
答:《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
《洛诰》:“周公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
称洛或洛邑,都可以。周人就一并用,都不错。——马执斌
2、问:贵室编写的初级中学第一册历史教科书其中第4课有姜尚其名,而史记清楚地记载是吕尚不知为何?
答:司马迁《史记》上说:“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索隐谯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可见,称姜姓、称吕姓,都可以。古人既有称其姓姜的,又有称其姓吕的。现在学术界也是如此。王宇信《西周》上说:“太公望名姜尚,字子牙,又叫姜子牙……因姜尚的祖先被封于吕地,所以又称他为吕尚。”《中国历史辞典》第页,“吕尚,即姜尚,姜太公,见姜尚条。”其主要事迹是在“姜尚”词条下讲述的。——马执斌
3、问:在现代汉语中,“夫”、“差”两字都是多音字。那么,当“夫差”作为吴王的名字这一专有名词时到底该怎样读呢?
答:《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十八 定公下解释:“夫差,阖庐嗣子。夫,音扶。”可见,“夫差”之“夫”,应读“fú”。“差”字,查多种书都未解释,可见一般我们读“chāi”是大
家认可的。记得田汉写的历史剧《胆剑篇》,人艺上演时,就是称吴王夫差为“fúchāi”。
——马执斌
4、问: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生产力显著提高,重要标志是铁制农具的出现,请问这一时期铁犁出现了吗?
答:春秋时期铁农具出现。如年湖南长沙出土一件铁臿,但当时还没有铁犁。进入战国时期,铁犁铧出现。如河南辉县出土一件铁犁铧。到战国中后期,河北、山西、山东都有铁犁铧出土。陕西临潼还发现两件秦国铁犁。——马执斌
选文一本文节选自袁腾飞《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1》
第一章青铜时代的中国人(先秦)5、五个想当老大的男人
管夷吾相齐
周王室东迁之后,势力一落千丈,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再朝觐和纳贡。到了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继位的时候,郑国的郑庄公不服,不去朝觐,于是周桓王带领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结果郑国部队力挫联军,周桓王战败,最惨的是他还被郑国大将一箭射中肩膀。小弟造反不能惩治,反而被修理了一顿,老大的威信自然一落千丈。从此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诸侯不再把他
当回事了。稍后,各路诸侯纷纷崛起,为了夺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
第一个起来称霸的是齐桓公。公元七世纪前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管仲又名夷吾,这个家伙从小品德不太好,打仗的时候人家都是往前冲,只有他往后跑,他总是以家有老母自己又是独生子为借口,对自己的逃兵行为进行解释。就连跟朋友一起做买卖,他也老算计人家。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务实
的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可以限制他。
管仲尤其反感漫无边际的高谈阔论,他在相齐的时候,有一句特别精彩的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段话对于今天的中国很有现实意义。用我们的话讲,你得先抓物质文明,然后再抓精神文明。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必然是相辅相成的。相反物质越富裕的地方,精神文明程度也就越高。齐国秉承着管仲的务实精神,加上地理位置良好,背靠大海,尽享渔盐之利,齐国很快就做大,成为诸侯
各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齐桓公甚至建立起一支多达人的常备军,按照以前的规定,诸侯国的军队规模不能超过人,而周天子自己的部队规模也不过才有人。所以可想而知,其他国家哪里是齐国的对手,但是齐国要
想对外扩张,也不能师出无名,所以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尊王攘夷”。
当时中原各国处在混战状况,觊觎中原已久的少数民族政权蛮、夷、狄、戎勾结起来,对华夏文明构成严重威胁。史书记载当时是“蛮夷与戎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华夏文明,命悬一线!当时的华夏文明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汉族的定居方式已经确立下来,农耕文明达到一定水平,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文字语言,这些都是蛮、夷、狄、戎所不具备的,如果这个时候华夏文明遭到灭绝,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这个时候谁能够站出来保卫华夏文明,谁就是保卫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保卫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卫了当时中原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民族的发型
管仲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使得齐国一下子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齐桓公出动大军先是打退了山戎对邢、卫两国的侵扰,救邢存卫,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其后,面对楚国南蛮的北向扩张,
齐国再度出兵会合中原国家的军队共同伐楚,解除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地区的威胁。公元前年,齐桓公葵丘会盟,周天子都派人来参加这个会盟,承认他的地位,使他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公认的第一
个霸主,齐国也正式成为第一个称霸的国家。
后来的孔子孔圣人,充满深情地讲:“管子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我们老百姓到今天都受到管仲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就要被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同化了。披发左衽是少数民族的服饰发式特点,披发就是披着头发,重环垂耳;左衽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是左边压右边。中原汉族人穿衣服是右边压左边,其实哪边压哪边都无所谓,但在中国古代,这个服装发型要一变,就意味礼制的崩坏,意味着国家要灭亡,道统要灭绝。这就是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的原因。
比如明末满人入关之后,发了一道剃发令,让汉族人改学满族人发型,一律削发留辫子,很多人不愿意,于是就遭到清兵的强迫镇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虾和熊掌不能兼得。即使这样,江阴城为了抵制剃发令,为了留发,抵抗了八十多天,全城被清军杀得尸横遍野。有对联为证:“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声赴死,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今天看来这件事有点过于荒诞,六万人同声
赴死,就为了这个发型。
以前的中国人一向把这个事看得特别重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不能乱动。年纪小的时候还可以剃头,冠礼成年之后头发就不能剃了,要蓄发蓄须,直到临终。所以崇祯皇帝在煤山殉国的时候,无颜
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以发覆面,头发散开才能拖到腰部那么长。如果没有管仲尊王攘夷,力保中原的话,当时的中原就被少数民族给同化了,发型一换,就轮不到后面这些事了。
周昭王喂鱼
继齐桓公称霸之后,晋文公和楚庄王陆续崛起。齐桓、晋文称公,因为齐国和晋国都是侯爵国,这个公不是它的封爵,而是尊称。楚庄称王是因为楚国乃子爵国,是南蛮少数民族政权,西周中期才被天子册封的。楚国国君嫌地位低,所以干脆自称为王,跟天子平起平坐。当时的天子周昭王不高兴了,亲自去楚国讨个说法。楚国人听说天子要来,准备了一艘船迎接他,周昭王特别高兴,以为楚国人害怕了,知道自己做错了。谁想到是因为楚国蛮人嫌周人扰民,设计用胶水粘的船身,昭王一上船才开了没多久就散架了,
周天子一众人全部落水葬身鱼腹。可见这个楚国的南蛮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民族。
周天子的南征失败导致整个东周的神话破灭,王朝由盛转衰。到了春秋晚期的时候,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竞相称霸。吴越两国在长江流域,吴国的都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越国的都城就在今天的绍兴。那个
时候,江南就已经开始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陆续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在历史上被统称为春秋五霸,个个牛叉。
选文二本文节选自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第二章城市跟你说·国家与城市
······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國”,是最早的國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國、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國,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第二章城市跟你说·大屋顶
城市好吗?难讲。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2]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我们民族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第二章城市跟你说·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
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
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自由是城市的特质。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
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读后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haikuoyua.com/ymzz/6844.html